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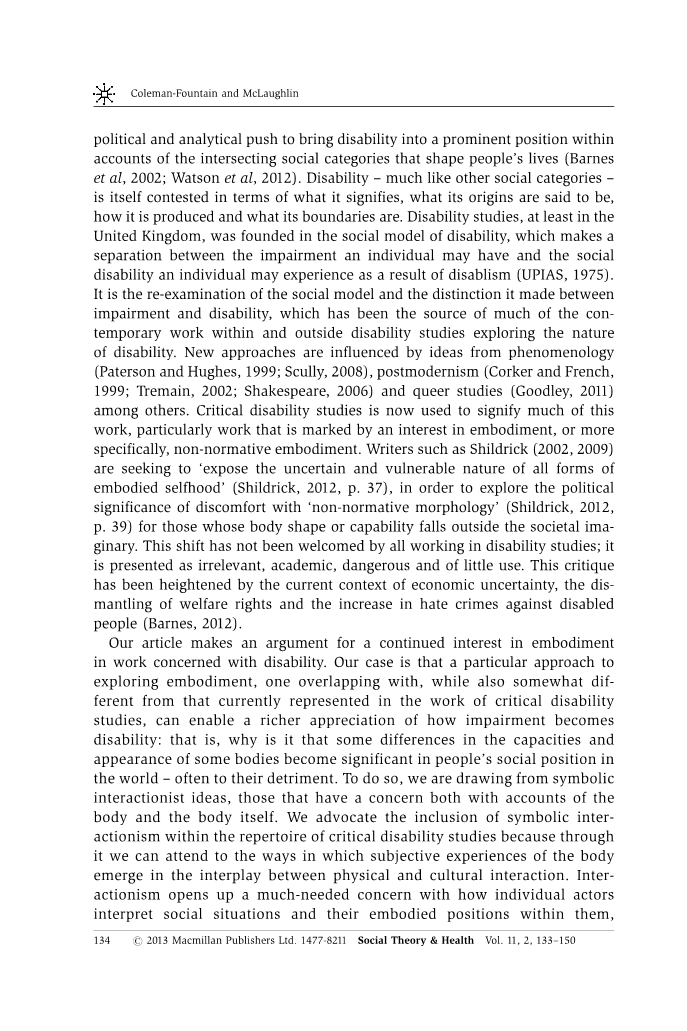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9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残疾的相互作用和损害
摘要:理论上,残疾工作正在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基于残疾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被认为是规律性强的,脱离政治的,并把残疾问题推动为塑造人们生活的,相互影响的,社会类别的重要地位。目前在关键的残疾研究中产生了是否应该包括危害和其带来的现象的辩论。本文认为,应该这么做,为了探讨身体可以做的事中有什么样的差异,应该从象征性的绘画互动主义和体现文学来做,从而定义损伤。在人们如何理解方面通过社交互动发挥作用。我们认为,这些日常的互动和我们对他们讲述的故事是产生损害和残疾重要的空间和叙事方式。互动和故事不仅在它们如何受到更广泛的社会规范,集体故事和社会规范的影响体制过程中很重要,也有助于他们有时提供抵抗点以及对这些规范,故事和机构的挑战。因此,损害和互动的意思是他们在有意识的自我认同和双方中所扮演的角色权力和不平等的更广泛的动力。
社会理论与健康(2013)11,133-150。 DOI:10.1057 / sth.2012.21;2012年11月14日在线发布
关键词:符号互动;残疾研究;实施案例; 损害;故事; 医学社会学
残疾与损伤的相互作用:不同实施方案的故事
介绍
理论上,残疾工作正在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基于残疾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被认为是规律性强的,脱离政治的,并把残疾问题推动为塑造人们生活的,相互影响的,社会类别的重要地位。残疾很像其他社会类别,就其所表示的意义而言,它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它的起源是什么,它是如何生产的,以及它的界限是什么。残疾研究,至少在英国,被认为是使得一个人可能具有的损害与社会之间的分离,一个人可能由于失势而遭受残疾残疾的社会模式。这是对社会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障碍和残疾的重新审视,这一直是残疾研究探索自然界内外残疾的许多临时工作的来源。新的方法受到现象学观念(Paterson和Hughes,1999; Scully,2008),后现代主义(Corker and French,1999; Tremain,2002;Shakespeare,2006年)和奇怪的研究(Goodley,2011)等等的影响。关键的残疾研究现在用来表示这一点工作,特别是对体现兴趣的工作,或更多具体而言,是非规范的实施方式。作家如希尔里克(2002,2009)正试图“揭露各种形式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体现自我(Shildrick,2012,第37页),以探索政治对“非规范形态”的不适感的意义(Shildrick,2012,39页)。对于那些身体或能力超出社会印象的人来说,所有从事残疾人研究的人都不欢迎这种转变。它被认为是不相关学术的,危险的和无用的。这个批评在当前经济不稳定,福利权利不受欢迎和仇恨犯罪增加的背景下更显得突出了(Barnes,2012)。
我们的文章在与残疾有关的工作中提出了对实体持续兴趣的论点。我们的情况是用一个特定的方法探索一个与之重叠的体现,同时也与目前在关键残疾研究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有所不同,它可以使人们更加认识到损害是如何变成的残疾: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现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变得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能力和一些身体的能力有一些往往对他们不利的分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从象征性的互动主义思想,那些与之相关的问题身体和身体本身出发。通过我们可以关注出现在物理和文化交互的相互作用中的身体主观体验的方式,我们主张把象征性的行动主义纳入关键残疾研究的范畴。国际行动主义开创了一个亟需关注的个人行为者解读社会情况及其内部的具体立场:认识到身体允许的不同能力,而不是减少残疾人的财产。
一开始,有一点很重要的声明是,我们关注的体现不应被视为仅仅在身体损伤方面等同于一种兴趣。相反,认知发展的一系列差异,行为和被认为是损伤的学习风格,也标志着自己以不同形式的身体表达和运动变得社会化,这在互动和边缘化和排斥过程中有重要意义。我们感兴趣的是各种各样的身体如何生活和被认为是受损的以及如何导致特定的互动动态和等级社会定位。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我们想要探索的核心:社会交往在身体的意义是如何形成的,
社会交往的意义如何发生。这意味着几个兴趣事情:每天的遭遇,个人的身份,身体和情绪,语言。虽然我们最初将花费一些时间来探索在这个微观层面上的互动组件,我们也会做的是在更大规模的权力动态展示这些互动,在监管,边缘化和歧视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通过绘制出戈夫曼的文章来开始这篇文章的研究,说明如何残疾作为差异的标志把人排除在 “其他”到“正常” 之外。对那些机构微观层面,互动的力量随之而来的意思理解为基于身体的物质性和所给的案例。然后我们通过询问当代对不同损伤的理解成为福祉等的机构,探讨受损的制度化,并且使塑造残疾人的生活变得重要。我们通过处理权力问题,以不同的方式所打开的,迎接挑战的潜力以及通过讲述新的损伤和残疾故事来“破坏”实体叙述。
构筑身体差异:戈夫曼的特征研究
符号互动主义在社会学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根源在实用主义和现象学,它是在二十世纪初从一个群体的工作成长起来的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Blumer,1937,1969)。它从一开始就对社会交往的动力和通过这些遭遇的人口创造“偏离”这两者都感兴趣。残疾一直是一个长期的利益,这是因为符号互动论者认为它不符合社会规范遭遇。戴维斯(1961)认为它产生了“粘性相遇”,因为在这样做的时候,残疾被定义为一种错误的形式(Becker,1973)。许多互动主义的焦点在于人如何避免残疾。因此,通过管理残疾而成为偏离的社会惩罚中断最小化(Sheehan,1968,1970; Lemert,1970)。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可有研究价值的残疾问题之一是欧文戈弗曼,一位在芝加哥芝加哥学派传统方面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提出的。他的经典文字特征是对发展偏离社会学的重大贡献,发展了许多当代社会学(Smith,2000)。他对社会交往的广泛分析一直是影响最大的。在残疾研究他的遗产,主要来自他的特征的工作,一直是一个观察“正常状态”的假设如何影响对待身体的社会反应(Wendell,1996; Titchkosky,2000)。戈夫曼主要理解为一种身体差异的形式,并不是固有的贬低,而是在相互作用中变得如此产生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归因于与身体感知中断的缺陷规范。正如史密斯(Smith,2000)所述,戈夫曼并不关心这个事实而是如何不同的背景构成特征不同的东西。别人认为这是一种特征,因为它造成了一个人假定的“虚拟”社会之间的差异身份及其“实际”的社会认同(Goffman,1990 [1963],第12页)。
戈夫曼对特征的分析已经证明对于探究“正常”体现文化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是有用的。Goffman(1990 [1963],第15页)认为,“正常的” 被认为是对那些“不偏离特定期望争议”的一种珍贵的文化地位。管理一个情况的物质期望被确定,戈夫曼后来将其描述为“框架”内化的社会期望,它构造了事件或“行为”如何被理解和理解。他认为,文化场景是通过“交际模式”而形成的(Goffman,1974)。在斯蒂格玛,戈夫曼认为,“正常”预示着一个人对身体的期望。这些期望不必然是普遍的,但要根据个人的经验转移不同形式的实施案例,如Goffman(1990 [1963],第46页)描述“自己”和“明智”。比如说(注意知道戈夫曼很容易使用他自己的术语),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先天受污染的孩子”的家庭谁从“贬低定义”保护这个孩子,以便产生他或他自己的“正常”的自我意识。当代作品继续借鉴戈夫曼的理解管理残疾人及其照顾者所造成的社会不适(de Klerk和Ampousah,2003; Anderson,2009)。 McLaughlin和同事探索了残疾儿童家庭如何管理负面情况别人对他们的孩子的回应(McLaughlin and Goodley,2008;McLaughlin和Clavering,2012)。同样,Scully探索“隐藏的劳动”残疾人承担谈判他人的不适,所以他们可能在互动中发挥作用。
这个“处理”包括控制一个人的自我呈现,识别对方需要知道或想要感受的东西,评估需要采取哪些策略并实施它们,依次产生所需的响应等等,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物理资源和心理能量(Scully,2010年,第31页)。
阿克顿和赫德从戈夫曼明确提出,探讨那些在社交互动中表现差的人面临的困难,并争辩说,用一个象征互动主义的方法进入差表现的社会学分析使我们能够产生个人创造的微观过程的例子,并保持“正常”和“污名化”之间的区别(Acton和Hird,2004)。
从Goffman和其他交互作者的工作中,我们想要探索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是怎样把特定的实例变得不同的,以及这些框架的含义是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立刻就把残疾问题解决成了个人问题和政治问题((Williams,2001年),并在这样做,提出了破坏或重新构思不同实现方式的方法。但是,在提出一个交互方法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各种作家提出互动主义的一个不能解决的难题:如果意义和身份出现在互动中,并且互动正在发生时间在不同的规模和复杂性的日常经历,如何做模式互动,自我和体现发展的力量的同时做到禁止其他互动,关闭可能想象和否认的事物替代生存和表演的方法的有效性?像Goffman这样的互动人物受到了残疾研究学者的批评(Oliver,1990; Abberley,1993;Wendell,1996)等(Bourdieu,1989; Reynolds,1993; Longmore,1998)为了政治本身对社会和物质背景的理解告知他们已经研究的交互。总的说来,内部行动主义者由于自己的特权而忽视了宏观结构性的问题构成“主观”日常生活的微观关系。除此之外,由符号互动主义方法产生的自我管理的叙述要么隐含地或明确地冒着验证现状的风险,意味着有一个机构参与了残疾人如何通过自己的表现和技能来实现互动。这样的成本和劳动力表演要求和不平等嵌入使人必须适应不太重视其他人的规范(Scully,2010)。
我们提出两种探索这个难题的方法来解释为什么它是分析性的,包括对社交互动的兴趣,是有价值的和政治上有用的当寻求理解残疾作为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类别:(i)重视在相互作用中检查机构的重要性,并探讨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物质性受损;(ii)如何通过账户进一步保证互动的规范由文化叙事和制度过程所产生,维系着文化如何评判和执行表演的不平等。
损害的问题
后结构主义账户,包括关键残疾研究中的账目,正确地强调把意思刻在身体上的过程互动的重要元素,因此也是我们的主观经验(Crossley,1996)。但是,我们与研究希望能够坚持受损和身体的问题相比,哪些地方有所不同地位和残疾问题在重大残疾问题上脱颖而出。该后结构主义思想对于发展关键残疾的意义研究导致专注于而不是参与身体本身。Scully(2008)回应,我们认为保留是重要的一些区别身体差异,障碍和残疾,因为我们要坚持一个机构是什么,和可以的差异具体细节,这事关重大。这种观点与古德利等其他作者(2001,2011)年的受损与实际情况没有实际的对应关系:
谈论受损或正常身体的“暴力事实”会唤起生物学的机制已经建成。监管准则欢迎对象假定位置。在这个表示之前,身体不是某个实体:它已经经历了一个表示的过程(Goodley,2011, 119页)。
古德利认为,损害不是身体的内在属性,相反,它是由诊断和标签类别生产的。因为唐氏综合征或其他类别的遗传疾病没有中性意义超越产生它们的医疗过程是真实的。我们遵循一些程度,特别是在医学定义如何是塑造和通知社交互动至关重要的因素类别。在这其中不断扩大的遗传学范围及其产生“本体论争议”的能力临界形式的疾病 “(Buchbinder和Timmermans,2011年,第57页)。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体的实际材料似乎是很难的事项。但是,我们离开古德利的的范围后发现,似乎是在争论这个机构从来没有这么重要。即使在遗传筛查的情况下,涉及诊断和交流结果的相互作用没有留在生物化学;例如在新生儿筛查或儿童中经过基因检测,父母对其基因版本有贡献,旁边的实际孩子的存在,都在影响遗传学家和日常生活中(McLaughlin和Clavering,2012)。
没有特定团体和推论之间的联系像健康,有吸引力,小孩,成人,同性恋,直系,这样的类别不能变得安全和具有社会意义。他们变得安全和社会通过他们对实际的身体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影响来说是重要的他们在互动阅读。女性主义社会地理学家长期以来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空间的性别化动力学中有所涉猎男人和女人“占据”他们周围的空间,并通过它创造
归属和排斥的界限(McDowell,1983; Davies,2003)。我们的自己的方法考虑到身体的重要性作为其一部分社交相遇。在这个方面,机构的外观和功能是非常重要的通知社会互动方式,并在人们在理解的规范框架内“合适”决定机构和决策方面至关重要。正如我们所见,以奥运希望者为例,比如Caster Semenya和Oscar Pistorius,身体被定义为“正常”或“其他”的方式依赖于身体在社交场合检查时的身体素质。
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比如古德利和希尔德里克所提出的分析强调赋予该机构意义的文化进程,包括失去意义,没有坚持身体本身的细节,错过了这些意义成为可能的三个重要方面保持。首先,某些形式的身体差异比其他形式更容易被视为特别的障碍。医学可能是强大的,但会努力让人们接受一个无法行走的解释当有问题的人是双截肢者时出现耳聋症状。这个可能看起来很容易,但我们不相信。这两个过程诊断和生活必须与存在的身体一起工作,当然不是社会交往中的因素不平等的生产者,意味着不是所有的现象都是可能的。正如莫尔(2002年,第24页)所指出的那样,有一个病人身体确实是临床诊断不可缺少的。这个是医药在生产中能保持的力量的重要限制损害和残疾。因此,当我们建议生物能源需要一个身体,我们正在身体里认识到意义投入的过程
全文共12164字,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1095],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