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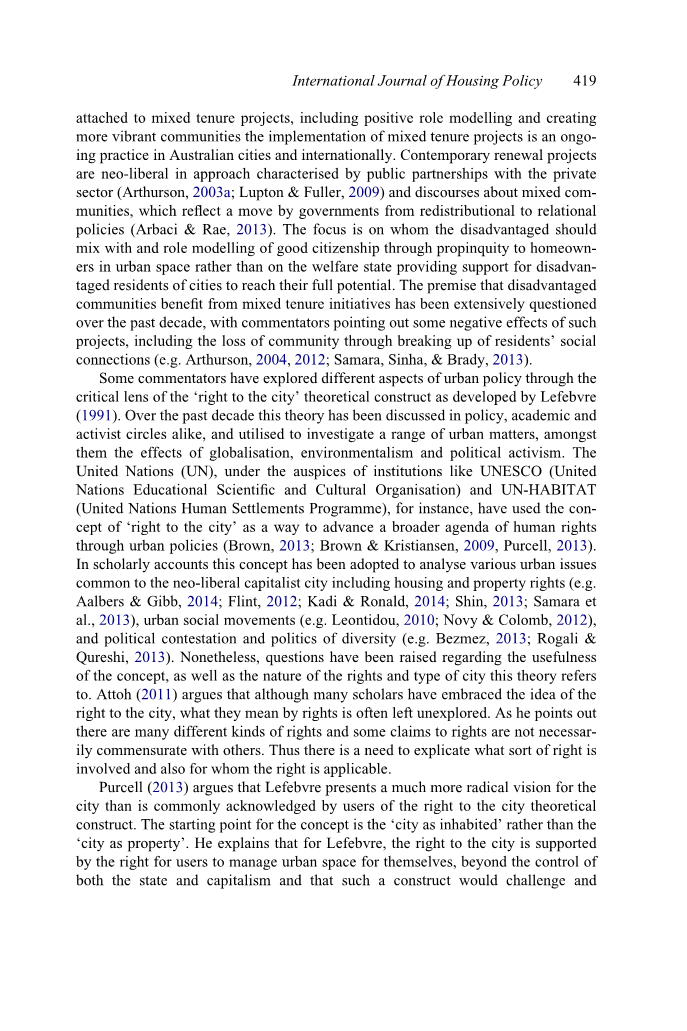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9 页
社会融合,“在真空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主意,但你必须正确地去做!”探索城市框架下的社会融合
凯西bull;亚瑟森*、艾丽丝bull;莱文和安娜bull;齐尔斯奇
弗林德斯大学医学院索斯盖特健康、社会与公平研究所,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尽管有人对基本假设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但在澳大利亚城市,实施混合土地使用权项目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实践。本文以澳大利亚墨尔本卡尔顿住宅区再开发项目为例,以列斐济尔的工作为组织框架,借鉴“城市权利”的概念,对社会混合政策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调查研究。从列斐济尔的工作中,我们了解到城市的权利是一种参与和影响决策的权利,以及享受和进入当地城市空间的权利。手机的资料包括对公共住房租户、私人住户和服务提供者的深入采访,以及社区观察和参与现场活动。调查结果显示,公屋租户影响及参与重建计划决策过程的机会有限,而公共空间私有化,对他们全面进入“开放”空间,造成了持续的象征性及实质障碍。在实施社会混合政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承租人参与和充分享受社区新设计开放空间的机会方面,出现了许多紧张情况;实际上,承租人被剥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
关键词:任期混合;公共住房;城市更新;城市使用权;社会融合
一、介绍
在澳大利亚和国际上,更新项目以提高位于城市和地区特定空间地理区域的老化公共住房集中度是司空见惯的。这些项目大多涉及将公屋租户迁往其他地区,以稀释弱势居民的集中程度,并创造混合居住的居住环境。尽管对基本假设和预期的可靠性提出了许多问题,结合混合土地使用权项目,包括积极的榜样作用和创建更有活力的社区,在澳大利亚城市和国际上实施混合土地使用权项目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实践。当代更新项目在方法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其特点是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Arthurson,2003年a;Luptonamp;Fuller,2009年)以及关于混合社区的论述,反映了政府从再分配政策向关系政策的转变(Arbaciamp;Rae,2013年)。重点是弱势群体应与谁融合,并通过与城市空间的业主的接触树立良好公民的榜样,而不是福利国家为城市弱势居民提供支持,使其充发挥潜力。过去十年来,弱势群体从混合终身制计划中获益的前提受到了广泛质疑,评论家指出这些项目的一些负面影响,包括由于居民社会关系的破裂而失去了社区(例如,Arthurson,2004、2012;Samara、Sinha和Brady,2013)。
一些评论家通过列斐济尔(1991)提出的“城市权利”理论建构的批判视角,探讨了城市政策的不同方面。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一理论在政策界、学术界和活动人士圈子中都得到了讨论,并被用于调查一系列城市问题,其中包括全球化、环保主义和政治活动家的影响。例如,联合国(联合国)在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和人居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等机构的支持下,利用“城市权利”的概念,通过城市政策推动更广泛的人权议程(Brown,2013;BRown和Kristiansen,2009年,Purcell,2013年)。在学术报告中,这一概念被用来分析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城市常见的各种城市问题,包括住房和产权(例如,奥尔伯斯和吉布,2014年;弗林特,2012年;卡迪和罗纳德,2014年;辛,2013年;萨马拉等,2013年)、城市社会运动(例如,利昂蒂杜,2010年;诺维和科隆,2012年)和政治竞争和多样性政治(如Bezmez,2013年;Rogaliamp;Qureshi,2013年)。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实用性,以及这一理论所指的权利性质和城市类型提出了质疑。Attoh(2011)认为,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接受了城市权利的概念,但他们对权利的含义旺旺没有加以探究。正如他所指出的,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权利,有些权利要求并不一定与其他权利相称。因此,有必要说明涉及哪种权利,以及该权利适用于谁。
Purcell(2013)认为,列斐济尔为城市提供了一个比城市权利理论建构的使用者普遍认可的更为激进的愿景。概念的出发点是“有人居住的城市”,而不是“作为财产的城市”。他解释说,对于列斐伏尔来说,城市的权利是由使用者自行管理城市空间的权利所支持的,而这种权利不受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控制,这种建设将挑战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产权。他设想的自我管理模式将超越国家和资本主义,由人们管理集体决策,而不是将决策交给国家官员。因此,列斐济尔的城市权是双重的,既包括参与决策和自我管理城市空间的权利,也包括对城市空间适当利用的权利,因为列斐济尔认为城市空间的权利属于公民,而不属于资本主义财产所有者:城市的权利并不是用户要求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城市有更多的访问权和控制权,后者是现有的一个更大的部分。相反,这是一种超越现有城市、培育城市以使其成长和传播的运动。(珀塞尔,2013年,第150页)
同样,哈维(2003年,第941页)对城市权利的愿景也将其描述为不再仅仅是一种“正确的房地产投机和国家规划者定义的权利”,而是一种积极的权利,即改变和塑造城市“更符合我们内心的愿望,并由此使我们重塑一个不同的形象”。虽然《城市权利》被用作分析框架,以探讨跨多个利益和规模的紧张关系,但不同的方法通常侧重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和权力不平等的空间表现(Pinnegar,2012年,第289页)。虽然普赛尔和哈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设想了列斐济尔对城市的权利,但有人认为需要多种解释,但“每种解释都应在其概念上具体化,并在其政治内容上透明化”(普赛尔,2013年,第142页)。
有一个新兴的,尽管越来越多的文学团体已经开始专门利用城市视角作为分析框架,来强调和探讨近期城市更新项目中的一些内在紧张关系、分配和公平问题,这些项目的目标是在澳大利亚城市和国际间建立公共住房地产。与珀塞尔一样,这些评论人士认为,未来的研究需要在这种公共住房重建的情况下,通过城市视角来调查不同的背景(Bezmez,2013年;Chaskinamp;Joseph,2013年;Samara等人,2013年;Sinhaamp;Kasdan,2013年)。本文以澳大利亚墨尔本卡尔顿房地产再开发项目为例,给出一种解释。
二、城市更新与城市权利
在制定当前研究的理论框架时,列斐济尔的城市权利概念被作为一种启发式工具,通过卡尔顿庄园的案例研究,获取和探索城市更新和社会混合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本节更深入地探讨了列斐济尔的论点,即城市的权利可以通过适当的权利或访问,充分利用当地城市空间以及居民参与有关城市空间生产问题的决策过程的权利来实现。我们还考虑了其他最近利用列斐济尔框架进行的城市重建研究。
1.进入、适当和充分利用当地城市空间的权利
列斐济尔(1991)认为,可以通过阶级形成的过程,阻碍进入当地社区和适当城市空间的权利。与探索城市更新房地产中的公共住房承租人的情况有关,城市空间所有权不是获得该权利的必要条件。一些进入城市空间的途径被拒绝,例如,通过中产阶级房主在特定的街区内发展私有化或封闭社区,在传统工人阶级地区中产阶级化的情况下转移贫困居民,在某些街区的穷人社区或私有设施及服务不与这些居民共享。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方式中,优势更大的居民可以控制自己与其他阶级群体的距离,并在选择居住在混合居住区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实践和价值观(Andreotti、Le Gales和Fuentes,2012年)。其他可能威胁到城市空间利用权利与城市重建有关的过程包括:弱势居民被迫搬迁、被他人羞辱或体验到不属于当地的感觉,从而使他们对进入当地城市空间感到不安。后一方面可能包括骚扰、敌意或无法进入当地空间等因素(Bezmez,2013年,第96页)。市场驱动的重建策略,包括当代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安排,将公共住房私有化,将产权和管理权转让给私人开发商,并依靠成功吸引中等收入的房主到邻近地区,也可能享有“交换价值取向”,这是对列斐济尔关于进入城市空间概念 的反对(Arthurson,2001年)。
正如Chaskin和Joseph(2013)所指出的,对于城市再生项目与当地空间使用权利之间得失关系,一个更积极的观点在再生项目的一体化方面有所暗示。社会整合主义者的理想与列斐伏尔的呼吁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列斐济尔呼吁结束城市空间中阶级之间的社会隔离。具体来说,通过混合使用权项目,弱势群体可以进入城市的部分地区,否则他们将无法进入,并与更多权利的邻居共同生活。杜克(2009年),在美国背景下利用城市框架的权利,同样认为,创造混合收入住房的项目有可能促进公共住房承租人对城市的权利,但前提是那些实施政策的人积极支持和制定战略,以应对业主和投资者对社区内公共住房的反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与被视为降低当地住宅整体价值的公共租房相比,购房者将房地产视为具有特定经济价值的投资,并且具有潜在的增长潜力,这两者之间产生了紧张关系。
综上所述,在城市更新对弱势公共住房居民社会空间权利的影响方面,出现了一些相关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实施混合住房使用权项目来减少公共住房使用权的物质隔离,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或减少居民利用当地城市空间的机会或融入社会的机会。
2.参与有关城市空间生产问题的决策过程的权利
列斐济尔关注的是参与有关城市空间生产问题的决策过程的权利,这也与城市更新场地上的公共住房承租人有关,城市空间的性质和生产得到了实质性的重建。当然,当代试图重建房地产和创建混合所有制社区的广泛言论承认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与社区合作的重要性。然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实践中往往是不明确和有限的。例如,在美国的背景下,Lucio和Wolfersteig(2012年)利用列斐济尔的框架来调查居民在“HOPE VI”方案发展的不同阶段参与该方案的权利。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参与决策和选址的权利不是方案设计的组成部分。同时,基于列斐济尔、Darcy和Rogers(2014年)的工作,他们认为,城市权利的概念可以被用作重新制定城市更新中涉及的民主进程的一种方式,以发展出更加民主的城市公民概念。然而,在他们对悉尼公私合作项目Bonnyrigg Living Communities的案例研究中,新自由主义议程贬低了租户的现有知识,因为专业社区建设者从租户那里获得了公民权利。
多项因素意味着,在当代公私住房委员会的合作关系中,要让居民参与市区重建,并承认他们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利益之间的分歧,这比以前更具挑战性。这些特征包括商业机密和其他与参与时间表相关的条款,这些条款促进权宜之计,往往会减少社区参与(Arthurson,2003b;Purcell,2003)。正如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再生伙伴关系也被主要的权力差异所渗透,大型资金充足的专业伙伴可以控制议程,这些议程可能影响其动员和排除决策过程中弱势群体声音的能力(Bezmez,2013年)。三、卡尔顿房地产重建项目
案例研究地点卡尔顿庄园位于墨尔本市东北部边界。它建于20世纪60年代,是当时维多利亚住房委员会(Tibbits,1988,第124126页)大规模贫民窟清理计划的结果。与许多其他房地产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广阔的地区逐渐成为一个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市中心地区,它在外人眼中也获得了负面的声誉。在重建工程展开前,房屋存量除了定期维修工程外,自原址兴建以来,并未得到改善,这使该屋群的外观受到忽视。这个庄园占地7.5公顷,有三个地块,分别是莱贡、吉宝和埃尔金。卡尔顿房地产再开发项目是一个公私合作项目,因此提供了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当代公私房再开发特点和紧张关系的典型例子。该计划于2006年开始实施,包括九个实施阶段,预计到2017年全面完成(人力资源部[DHS],2014a)。除了重建公共房屋(拆除低层建筑物和翻新现有高层单位)外,该项目还包括建造一个退休村、养老中心和新的公共公园,以及改善花园和景观。
研究项目的重点是利贡地块(第1阶段),因为这是研究开始时唯一完成的综合体(2011年6月完成),公共和私人居民都搬入了该住房。在重建之前,该地块包括八幢四层楼的无电梯建筑,2006年被拆除。重建后,它包括三个相邻的建筑物,一个公共房屋建筑和两个私人建筑,面向不同的街道,但共同围成一个公共室外花园空间。公共住宅楼高8层,两栋私人公寓楼高4层,与公共住宅楼有单独的入口和停车场。
表1总结了重建前后的单位数量
卡尔顿地产、重建前和重建后的公共和私人单位数量
重建前 重建后
|
住宅小区 |
公共单位 私人单位 |
公共单位 私人单位 |
|
莱贡庄园1期 |
128 0 |
84 98 |
资料来源:DHS(2014a)
表2 研究参与者N D 51
|
|
面谈 |
|
居住在重建综合楼内的公屋租户 |
21 |
|
没有返回重建综合大楼的公屋租户 |
10 |
|
居住在重建综合楼的私人居民 |
10 |
|
政策制定者和服务提供商 |
10 |
|
合计 |
51 |
研究项目于2011年初开始,包括定性和定量方法:对房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