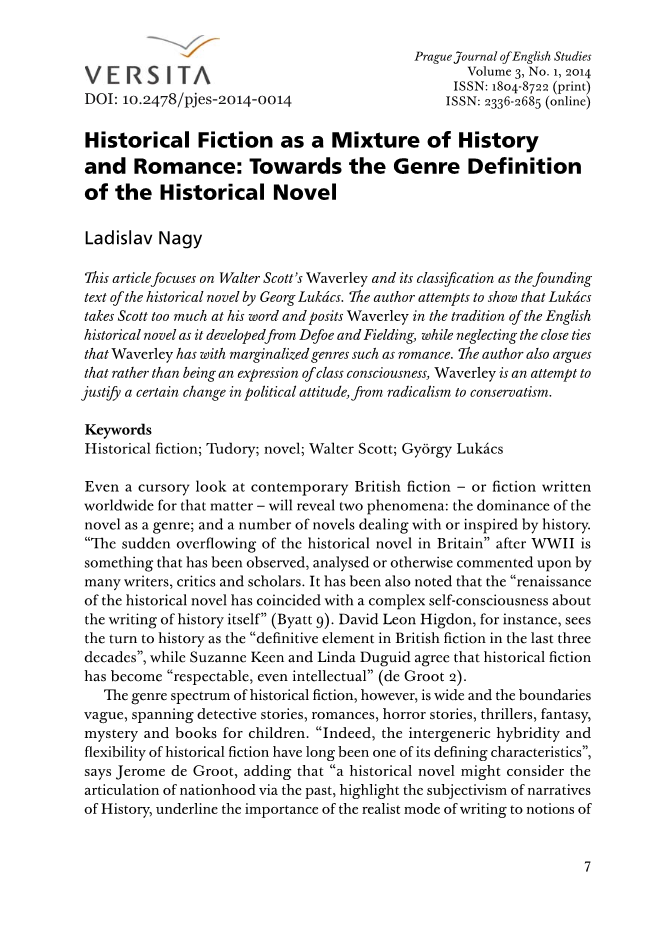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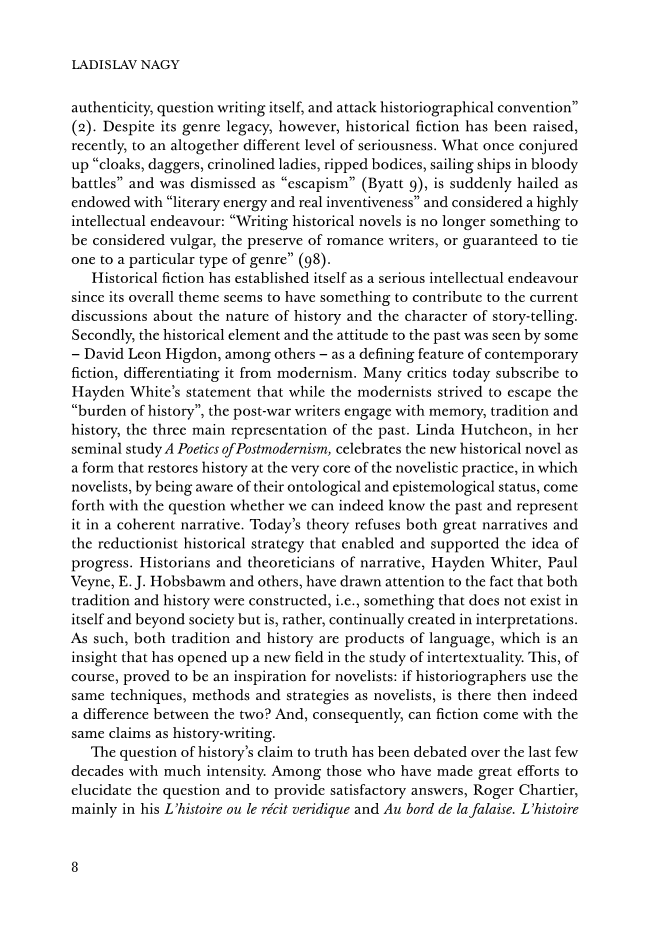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1 页
历史与浪漫融合的历史小说:走向历史小说的体裁定义
Ladislav Nahy
本文重点介绍沃尔特·斯科特的《韦弗利》及其作为乔治·卢卡奇历史小说的创始文本的分类。作者试图表明,卢卡奇对斯科特的言论过于苛刻,并将《韦弗利》置于英国传统历史小说中,因为它是从迪福和菲尔丁发展而来的,而忽略了《韦弗利》与边缘化流派如浪漫的密切联系。作者还认为,《韦弗利》表达的不是阶级意识,而是试图证明政治态度的变化是合理的,这种态度的变化主要是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
关键词:历史小说;都铎;小说;沃尔特斯科特;捷尔吉·卢卡奇
即使粗略地看一下当代英国小说,或者全世界为此而写的小说,也会揭示出两种现象:小说占据了一种流派的主导地位;以及一些小说受到了历史启发。二战后“英国历史小说突然泛滥”是许多作家,评论家和学者观察,分析或评论的观点。人们还注意到,“历史小说的复兴恰逢对历史本身写作的复杂的自我意识的觉醒”(Byatt 9)。例如,大卫·莱昂·希顿(David Leon Higdon)认为:历史的转变是过去三十年英国小说中的“权威因素”,而苏珊·基恩和琳达·杜吉德同意历史小说已经变得“受人尊敬,甚至是理智的”(de Groot 2) 。
然而,历史小说的流派范围很广,界限模糊,涵盖了侦探故事,浪漫故事,恐怖故事,惊悚小说,幻想,神秘和儿童书籍。“事实上,历史小说种类的混合性和灵活性长期以来一直是其定义的特征之一”,Jerome de Groot说道,“一部历史小说可能会考虑过去对国家的阐释,强调历史叙事的主观主义,强调现实主义写作模式对于概念具有重要性和真实性,写作本身可能会攻击历史习俗“(2)。
但最近,历史小说已被提升到完全不同的严肃程度。曾经让人想起“斗篷,匕首,娇小的女士,撕裂的衣身,帆船在血腥的战斗中”,并被解释为“逃避现实”的历史小说(Byatt 9),突然被誉为具有“文学能量和真正的创造力”,并被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所创造出的:“撰写历史小说不再是一种被认为是低俗的东西,它将浪漫保留下来,并将其与一种特定类型的流派联系起来”(98)。
历史小说已经成为一种严肃的知识分子会为之努力的文学体裁,因为它的整体主题似乎有助于当前关于历史本质和文学故事性质的讨论。其次,有些人从中看到了过去的历史因素和态度,David Leon Higdon说,历史小说作为当代小说的一个定义特征,将其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今天许多评论家赞同海登怀特的说法,即使当现代主义者努力摆脱“历史的负担”,战后的作家们仍将记忆,传统和历史作为过去的三个主要表现。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在她的开创性研究“后现代主义诗学”中,将新的历史小说作为一种形式,将历史恢复到小说实践的核心,在这种形式中,小说家因为意识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地位,而质疑我们是否确实能够了解过去并以连贯的叙述来表达过去。今天的理论拒绝了伟大的叙事和简化的历史战略,这种战略能够支持进步的观念。历史学家和叙事理论家Hayden Whiter,Paul Veyne,EJ Hobsbawm等人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传统和历史都是建构的,即一种本身并不存在于社会之外,但又不断创造的事物。因此,传统和历史都是语言的产物,这是一种洞察力,开辟了互文性研究的新领域。当然,这被证明是小说家的灵感:如果史学家使用与小说家相同的技巧、方法和策略,那么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差异吗?因此,小说可以与历史写作一样具有相同的主张。
历史上对真理的主张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受到激烈的争论。在那些努力阐明问题并提供满意答案的人中,Roger Chartier主要是在他的文章中建议我们用充分性来取代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然而,总是将其视为所提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选择方法和所研究的来源,这对于提供答案几乎没有帮助。然而保罗利科虽然没有达到海登怀特那么深刻的研究,却强调了叙事的重要性,他在卡西尔之后声称,叙事是必然使用一个情节,我们的无形,模糊和沉默的体验都被预示。
本文的目的不是争论过去几十年的所有历史小说是否都考察了历史真相与虚构叙事之间的混乱关系,因为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相反,我想论证历史小说总是具有一些吸引力,并从事实和想象之间的模糊分歧中推动了它自身的发展。我想说,这种紧张关系恰恰是为历史小说的提供了它们所需要的文学力量以及促使它们成为经典。我不认为有必要讨论所有历史小说,正如琳达哈钦所做的那样,作为史学元小说。相反,我认为,值得密切关注每件作品的类型特征,以及作者与文学经典之间的工作关系进行谈判的方式,并通过区别于他人来证明他们对真理的主张。由于上文简要提及的过去几十年的理论框架被证明是对历史小说的一种解放影响,因此这一点更为紧迫。Hayden White,Paul Veyne和Michel Foucault对历史写作的“客观性”及其对真理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在批评中,Linda Hutcheon(强调历史元小说),Brian McHale(后现代本体论),Charles Jencks(后现代古典主义),Fredri Jameson(后现代模仿),最近由Mariadele Boccardi(历史小说和民族认同),Amy J. Elias(后现代意识作为创伤后意识,重新定义实证主义或“历史作为历史崇高 ”(Elias xviii)和许多其他观点。确实,历史小说已经达到了新的紧迫感。它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有娱乐功能,而是具有更多的东西:关于我们的过去及对我们现在影响方式的陈述,努力解开我们尚未能够看到的过去,甚至,给我们一个不同的过去,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掌握一个人的身份的机会。但是,在讨论历史小说时它对历史小说的贡献不应忽视历史小说的遗产和起源,而这种遗产和起源比看似复杂得多。
也许所有历史小说都很容易,仅仅因为它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就被归类为 “历史小说”,并按照Gyouml;rgyLukaacute;c设定的方式进行解释,他将历史小说视为一种独立的类型,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个卓越的流派,沃尔特斯科特是其创始人。然而,卢卡奇对斯科特所说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黑格尔遗产,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的历史小说理论是否被他所提倡的那种文学所证明是错误的。努力研究“描绘历史总体的历史精神与伟大文学体裁的交汇点”(9)在今天的背景下肯定会被认为是可疑的。此外,卢卡奇的格言“对民族独立和民族性格的诉求必然与重新唤醒民族历史,回忆过去,过去的伟大,国家的耻辱时刻,这是否会导致进步或反动的意识形态有关“(23)只有理所当然地认定特定的知识框架,即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时才是可以理解的。
卢卡奇把《韦弗利》作为历史小说的创始文本,并大胆地说“这里最重要的是历史意识越来越强烈,人们在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中对人类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历史课堂的斗争是否在人类进步中发挥了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肯定不是斯科特在《韦弗利》提出的问题。之后,卢卡奇提出了另一个大胆的主张:“斯科特的历史小说是18世纪伟大的社会小说的直接延续。”以及,“斯科特努力通过角色来描绘历史的斗争和对抗,在他们的心理和命运中,总是代表社会趋势和历史力量“ (30-33)。
这些陈述以多种方式提出问题。首先,要说斯科特建立在18世纪伟大的社会小说的基础上还有待证明。斯科特在序言中的主张是,他的书与浪漫有很大的不同,并且与小说很接近,即它是现实的,但就其他类型的特征而言,《韦弗利》实际上更接近早期的浪漫。例如,同名英雄的角色与汤姆琼斯或摩尔弗兰德斯等人的距离相当遥远,并且在整本小说中表现得很少,除了他的事实。放弃他的浪漫理想,采取保守的立场是愚蠢的。对于第二个陈述也是如此:如果《韦弗利》代表一种社会趋势,那么在拿破仑垮台后席卷整个欧洲的大规模保守主义浪潮在英国通过领先的第一代采取保守主义的观点来代表,因此,浪漫主义者被第二代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抛售,即黑兹利特,亨特和雪莱等作家。Lukaacute;c似乎在这里应用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一个人与他的班级一起被认同,随后,这个“班级”的故事与个人发展的故事一样被阅读,我们在迪福,菲尔丁,理查森和斯特恩的小说中找到了这个故事。因此,对于卢卡奇来说,这部历史小说成为了卓越的小说。在小说崛起的传统视角中,正如Ian Watt在其1949年出版的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小说的体裁形式与个人意识的兴起,与18世纪后期的商业风气和个人主义密切相关,在卢卡奇的框架里,它成为时代精神和某种阶级(“资产阶级”)意识的表达。我认为,这是卢卡奇绝对必要的作者以及为什么韦弗利作为(高度政治化)的联系之间的主要原因。现在和过去:“因此,历史小说中重要的不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的复述,而是那些在这些事件中发现的人的诗意觉醒。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重新体验导致人们思考,感受和行动的社会和人类动机,就像他们在历史现实中所做的那样“(27)。卢卡奇认为斯科特的《韦弗利》是第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他严格地将其与浪漫主义时期的历史化浪漫区别开来,例如哥特式小说,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可以看作是“恋物癖”。然而,卢卡奇似乎对斯科特的态度过于苛刻,因为将《韦弗利》归类为独立体裁的创始文本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斯科特明确表示这个故事是用六十年的距离叙述的,即足够的简短的理解时期,但同时,远远超过个人记忆的视野;第二,斯科特明确地对待历史主题以及历史与现在之间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种类型,斯科特的文本远非同质。它不仅仅是迪福,菲尔丁和理查森的经典小说,它回应了“超文本”元素,例如笔记,评论,民间传说的样本,即《韦弗利》与当代小说中的大部分内容。斯科特的小说出现在一个以历史主义为特征的时期的黎明时期。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历史与虚构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被理解为虚构角色的任何叙述都不算什么,甚至在前一时期也得到了很多讨论。早期小说(主要是迪福)和历史辩论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罗伯特梅耶在他的历史和早期英国小说,从培根到笛福的事实问题。梅耶引用迈克尔·麦克基恩的话说,这部小说“辩证地由浪漫与历史之间以及竞争认识论和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辩论构成”(13)。
Mayer认为这种小说的概念无法解释与历史和小说之间差异的讨论的密切联系。Mayer继续沿着这一论点一直走向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例如,威廉卡姆登),并用他们的例子来说明历史和小说之间的明显区别是多么模糊和历史无根据。近两个世纪以来,轮廓模糊不清,主要标准远不是一个可以得到资源支持的“客观”真理。相反,第一批研究实际历史资料的学者被贬低为是“古董”,他们的工作被嘲笑作为“发霉的”(托马斯·纳什)或者“收集了一些随意逃脱时间沉船的历史遗留物”(弗朗西斯·培根),而真实的历史是考虑到其他方面的,不管是实用的(培根)、国家利益(丘吉尔和其他为蒙茅斯的杰弗里辩护的人),可读性或维护特定社区的现状(着名的例子是理查德高夫的“迈德尔的历史”)。Mayer建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阅读早期的英国小说,例如鲁宾逊漂流记。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更接近著名的传记,如克拉伦登或哈钦森的传记。通过发音“我”,以一种表演的方式单独保证真实性(当个性在洛克斯术语中被定义为意识的同一性时):我是这些事件的直接见证,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我将它们叙述给你。正如Ian Watt所展示的那样,这正是现代小说诞生的个性,个体意识和独特性。然而,以瓦特为特征的这部小说有一个更为特殊的特征:它在范围和多样性的宽度上捕捉现实,人们可以补充、加强其对真理和真实性的要求。“如果说这部小说只是因为它看到了生活从阴暗的一面来说是现实的,它只会是一个倒置的浪漫;但事实上,它肯定试图描绘人类经验的各种变化,而不仅仅是那些适合某一特定文学视角的变化:小说的现实主义并非如此,它存在于它所呈现的那种生活中,但却以它呈现的方式存在(11)。瓦特强调了上面提到的“个人经历”,它总是独特的,新的,和历史事件一样,它不同于现成的模式或神话结构和情节。瓦特说,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必须是无形的,“小说的正式惯例的贫困似乎是它必须为其现实主义付出的代价”(13)。对“我”的真理的主张是基于更广泛的清教徒框架,其中发言者,叙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打开他们的灵魂并向读者展示他们的道德存在(75)。在18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似乎又回到了关于史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讨论。大卫休谟认为,史学和史诗在行动的统一性上存在“不是实物而是在程度上”,休·布莱尔认为,历史的作用是通过事实来教导,在话语中存在小说和浪漫的空间,因为他们可以承担教学角色。亚当·斯密也对这个问题有相同的看法,他说,历史的特点是与事实的关系,其作用是教导,而小说和浪漫是诗歌发明的产物,他们的任务是娱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被看见的原因。史密斯认为,对于话语,它们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文人的态度恰恰相反。他们强调文学的重要性,并以亚里士多德或后来的菲利普西德尼提出的论点为基础。威廉·戈德温认为“浪漫”是历史的一种,因为虽然历史学家只写一个单一的事件和一个人,但作家从许多来源收集他们的材料。戈德温更进一步强调:“浪漫”的作者是他真实历史的作者,亚历山大,凯撒,西塞罗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历史丰富。然而,最有见识的人对他们的尊重程度有多大?或许他们所有的性格都被歪曲了。因此,在每次特定交易中尊重其动机的猜想必须永远是错误的。浪漫的作家在这方面站在更高的地位。我们自然应该允许他理解他自己喜欢的生物的性格。浪漫主义作家被认为是真实历史的作家;虽然他以前被称为历史学家,但他必须争取下台进入他的竞争对手的地方,这个劣势,他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没有那个属于那个物种的艰苦,热情和崇高的想象力组成。这里感兴趣的是类型术语。当然,卢卡奇称《韦弗利》是一部小说,并认为它与浪漫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斯科特的关系相当含糊不清。一方面,他努力说服他的读者,他正在写一本小说,即一篇在时间和地点明确定义的严肃文学作品(在这方面,《韦弗利》与哥特小说有很大不同,后者位于只是模糊地设置在一些永恒的中世纪),并且他甚至没有试图掩饰他对浪漫的蔑视。在序言中,他反对他们的工作并指责他们呈现一个“贬低”的历史图景。“浪漫”这个名字是先验地被排除在外,因为它表明了轻浮,无关紧要。并不是每个小说读者都不会想到比Udolpho更少的城堡,其中东翼长期无人居住,而且钥匙要么丢失,要么托付给一些年迈的管家或管家,他们在第二卷中间的颤抖的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