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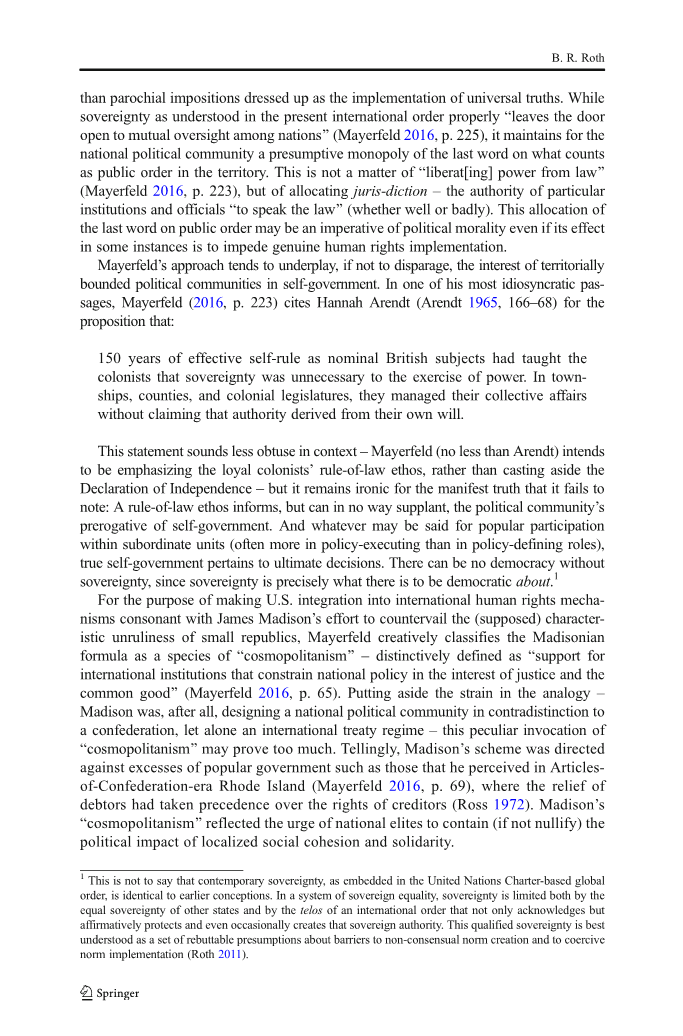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5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揭开主权、民主与人权
杰米·梅耶菲尔德的《人权承诺》适时纠正了人们对国际人权法与美国主权和民主关系的长期误解。当“美国例外论”以新的和更尖锐的形式重新出现时,作为对遵守国际法律约束的规范性挑战,梅耶菲尔德让我们想起了美国民主的根源是麦迪逊主义,这个传统主义强调自治的复杂挑战以及对权力集中度进行检查的需要。梅耶菲尔德正确地指出,国家主权并不是排除国际法律义务,而是在履行此类义务时所行使的权力(梅耶菲尔德 2016,p.219),而乔治·布什政府在起诉全球反恐战争中回避国际标准(最明显的是在对被拘留者待遇方面),代表了对美国基本政治原则的背叛而不是肯定。除了有揭穿这一真相的功能以外,梅耶菲尔德的书还巧妙地揭示了美国对国际法的抵制,不仅体现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酷刑备忘录》(而且显然是不诚实的)的主张中,而且还体现在美国关于国际和国内法律秩序之间关系的普遍教义中——促使人们违反了美国人一贯奉行的标准(即使并非始终如一地遵守)。
梅耶菲尔德热情洋溢地拥护符合主权和民主原则的国际人权法,然而不必要地贬低了自治国家政治团体和民众参与决策的道德意义。他在强调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紧迫性时,没有承认规范性考虑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使他想讲的直截了当的故事复杂化。更加平衡的做法将更仔细的区分人权本身与以人权名义行使权力;后者可能只不过是装作实现普遍真理的狭隘的强加。虽然目前国际秩序中所理解的主权适当地为各国之间相互监督敞开了大门(梅耶菲尔德 2016,p.225),它为国家政治社会维持了对在该领土上什么是公共秩序的硬道理的推定垄断。
这不是“从法律上解救权利”的问题(梅耶菲尔德 2016,p.223),而是一种分配管辖权——特定机构和官员“讲法律”的权力(不管是好还是坏)。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其对公共秩序的最后一句话的分配可能会影响政治道德,即使其后果是阻碍真正的人权实施。
梅耶菲尔德的做法往往会削弱(即使不贬低)自治政府的领土政治利益。在他最特别的一段话中,梅耶菲尔德(2016,p.223)引用汉娜·阿伦特(阿伦特 1965,166-68)的主张:
150年来,作为名义上的英国臣民,有效的自我统治告诉殖民者,主权对于行使权力是不必要的。在乡镇、县和殖民地立法机构中,他们管理着自己的集体事务,却没有宣称权威是根据自己的意愿产生的。
该声明在上下文中听起来不那么晦涩——梅耶菲尔德(比阿伦特更甚)打算强调忠诚的殖民者的法治精神,而不是抛弃《独立宣言》——但对于它失败的明显事实仍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治精神是必须的,但绝不能取代政治团体的自治权。不管说什么要在下属单位中普遍参与(通常在执行政策中比在决策角色中更多),真正的自治与最终决定有关。没有主权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主权正是要民主的目标。
为了使美国融入国际人权机制,与詹姆斯·麦迪逊努力消除(假定的)小共和国特有的不公正性相一致,梅耶菲尔德创造性地将麦迪逊公式归类为“世界大同”的一种——特别定义为“支持为了正义和共同利益而限制国家政策的国际机构”(梅耶菲尔德 2016,p.65)。抛开这种类比的压力不谈——毕竟,麦迪逊是在设计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而不是一个联邦,更不用说一个国际条约制度了——这种对“世界主义”的特殊援引可能证明太多了。显然,麦迪逊的计划是针对人民政府的过剩行为,例如他在《联邦时代的罗德岛公约》(梅耶菲尔德 2016,p.69),其中债务人的救济优先于债权人的权利(罗斯 1972)。麦迪逊的“世界大同主义”反映了国家精英的强烈愿望,即遏制(如果不是消除)地方社会凝聚力和团结的政治影响。
“世界大同主义”一词,无论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与普遍正义之间有多大联系,都可以被认为具有更深层的含义:放松束缚政治共同体的联系,以至于成员资格基本上变成交易性的。因此,相互责任实际上被有效地减少为私法义务(例如合同、赔偿、侵权)。这种发展可能为自由主义者们所喝彩,但它应该给社会民主人士带来麻烦。共同承诺抵制经济不平等、物质不安全和社会分层——建立一个明显属于所有居民的共同空间,同样以系统、密集和不封闭的共同责任为前提,这反过来又以一个有限的政治共同体为前提,这个共同体会形成一种集体认同感。这些居民在领土公共秩序条款的斗争中有着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有特殊(如果不一定是排他性的)地位参与制定这些条款的进程。
梅耶菲尔德公开反对政治参与在规范人权规范中的作用。也许他最具有挑衅性的主张是:从公共审议中推导出人权就是人权的消亡。人权是任何健康的公共协商形式的先决条件(梅耶菲尔德 2016,p.202)。为了避免让读者认为梅耶菲尔德有一个开放的标准,他详细阐述了如下(梅耶菲尔德 2016,p.198):
如果我们在公开审议之前坚持认为人民有权免于受到宗教迫害,审查制度,任意监禁,不公正审判,死刑,奴役以及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特别是酷刑,那么就没有值得抱怨的公共自治限制;他们有权享受教育、经济生活、医疗保健和体面的劳动条件。
梅耶菲尔德显然不愿意将奴隶制和酷刑与名单上的其他人区分开,即使前者似乎更可能获得广泛的共识。他提出的“什么不应列入立法议程”的标准,不是基于共识,也不是基于对特定集体决策过程结果的尊重,而是基于这一命题的道德真理。
正如梅耶菲尔德正确指示的那样,民主绝非可简化为多数制的。一个人只需要考虑掠夺性多数主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一票的表面政治平等会导致少数群体被剥夺甚至毁灭。这种结果(除其他事项外)完全否认少数人对其影响其切身利益的决定具有影响力,这将与任何公认的政治平等截然相反。但是尽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其他方面,对于什么是民主的基本特征,都没有达成共识,正是因为任何深思熟虑的民主概念都包含实质性和程序性的组成部分。(实话实说,即使选择程序性组成部分也是因为它们会导致一系列实质性后果而被选中,而长期或严重的未能实现这些后果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对程序的忠诚度。)
梅耶菲尔德在一系列有关教育、经济生活、医疗保健和有尊严的劳动条件的政策上公开地规定了民主的合法性。不幸的是,有诚意的有合理理由的知情人士不同意在这些领域的可接受政策范围内的政策,也不同意在公民自由甚至正当程序领域的细节和优先事项。但是对于梅耶菲尔德来说,对这些问题的民主答案不是来自民主决策程序中得出的任何答案,而是正确的答案。
梅耶菲尔德把自己对一个政府秩序的忠诚视为该秩序对正义核心问题的客观正确答案的倾向,这并不一定是错误的。他也不一定会错误地认为存在着关于正义的正确和可知的答案,政治道德的基本要素可能和梅耶菲尔德想象的一样客观,也可以通过锻炼理性来辨别。但是这些主张无助于设计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之间的合作体系。道德分歧的客观事实具有客观后果——包含客观的道德后果(考虑到合作破裂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合作需要超越实质性分歧,尽管双方对致力于某种权威决策过程(无论是大众还是精英)的共同承诺。
对此,杰里米·沃尔德隆的讽刺意味十足:有些决定太重要,不能以多数票通过,他们应该由最高法院做出五比四的决定。换句话说,权利对民主的中心性本身并不建议将权利决定从选民转移到精英机构。然而,需要有一个无党派的理由,在这个理由上,持有相互矛盾的实质性意见的人可以合情合理地联合起来,赋予一个特定的精英机构就一系列特定问题做出决定的权力。如果决策机构的选择被视为任何派系意识形态“”的产物,那么在敌对派系眼中,决策机构将自动失去合法性,而竞争派系则会完全有理由认为权力的转移是一种篡夺。
在赋予国内法院对立法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方面,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挑战。如果审查机构是外部的,并且不受政治界历史和文化发展长期趋势的影响,这就更加困难了。在这种背景下,对将权力让渡给国际人权机构的某些保证并非没有道理。
《人权承诺》的主要目的不是针对最新的主权概念,而是针对过时和扭曲的概念,这种概念由于对国际标准和程序的漠不关心而使等级道歉合理化。这是一本非常出色的书,偶尔(而且并非没有挑衅)转向言辞过多,而忽略了在出现更接近的问题时需要解决的考虑因素。(我不接受一句格言,即巴德案构成坏的法律,但极端的案件会产生坏的格言。)最终,梅耶菲尔德的呼吁不是要国际人权机构至高无上,而是要让国家立法机构要与这些机构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梅耶菲尔德 2016,p208-09)。确实,这是极好的建议。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37005],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