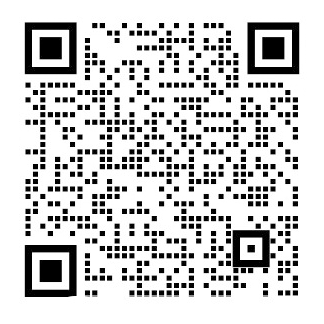意识形态和课程外文翻译资料
2022-08-08 20:23:03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Apple M, Apple M W.
2.Ideology and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production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production
Many economists and not a few sociologists and historians of education have a peculiar way of looking at schools. They envision the institution of schooling as something like a black box. One measures input before students enter schools and then measures output along the way or when “adults” enter the labor force. What actually goes on within the black box—what is taught, the concrete experience of children and teachers—is less important in this view than the more global and macro-economic considerations of rate of return on investment, or, more radically,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While these ar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perhaps especially that dealing, as I noted in Chapter 1, with the role of the school as a reproductive force in an unequal society, by the very nature of a vision of school as a black box, they cannot demonstrate how these effects are built within schools. Therefore, these individuals are less precise than they could be in explaining part of the role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the reproduction they want to describe. Yet, as I shall argue here, such cultural explanations needtobe got at;but it requiresadifferentbut oftencomplementary orientation than the ones these and other scholars employ.
There is a unique combination of elit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schools. As institutions they provide exceptionally interesting, and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potent, area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mechanisms of cultural distribution in a society. Thinking of schools as mechanisms of cultural distribution is important since, as the Italian Marxist Antonio Gramsci noted, a critical element in enhancing the ideological dominance of certain classes is the control of the knowledge preserving and producing institutions of a particular society. Thus, the “reality” that schools and other cultural institutions select, preserve, and distribute may need to be particularized, in Mannheimrsquo;s words, so that it can be seen as a particular “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may not serve the interests of every individual and group in society.
Now it has become something of a commonplace in recent soci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literature to speak of reality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 By this, these scholars, especially those of a phenomenological bent, mean two things. (1) Becoming a person is a social act, a process of initiation in which the neophyte accepts a particular social reality as reality tout court, as the way life “really is.” (2) On a larger scale, the social meanings which sustain and organize a collectivity are created by the continuing patterns of commonsense interaction of people as they go about their lives.3 Now this insertion of the social element back into wha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psychological problem in Anglo-Western society is certainly an improvement over the view of many educators who hold that the patterns of meanings which people use to organize their lives and attempt to transmit through their cultural institutions are independent of social or ideological influences. The notion that there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s a bit too general, however, and not as helpful as we might think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s that exist between cultural institutions, particularly schools, and the framework and textur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orms in general. As Whitty succinctly puts it,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notion that reality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seems to have led to a neglect of the consideration of how and why reality comes to be constructed in particular ways and how and why particular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seem to have the power to resist subversion.
Thu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does not explain why certain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and not others are distributed through schools; nor does it explain how the control of the knowledge preserving and producing institutions may be linked to the ideological dominance of powerful groups in a social collectivity.
The opposite principle, that knowledge is not related in any significant way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is also problematic, of course, though this may be a surprise to many curriculum theorists. This is best stated by Raymond Williams in his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e.
The pattern of meanings and values through which people conduct their whole lives can be seen for a time as autonomous, and as evolving within its own terms, but it is quite unreal, ultimately, to separate this pattern from a preci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which can extend its influence into the most unexpected regions of feeling and behavior. The common prescription of education, as the key to change, ignores the fact that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education are affected, and in some cases determined, by the actual systems of [political] decision and [economic] maintenance.
Both Whitty and Williams are raising quite difficult issues about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y and school knowledge, yet the context is generally British. It should not surprise us that there is a rather extensive history of dealing with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ulture and control on the Continent and in England. For one thing, they have had a less hidden set of class antagonisms than the USA. That the tradition of ideological analysis is less visible in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cholarship speaks to two other concerns though, the ahistorical nature of most educational activity and the dominance of an ethic of amelioration through technical models in most curriculum discourse.6 The ahistorical nature of the field of curriculum is rather interesting here. Anyone familiar w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意识形态和课程
Apple M, Apple M W.
2.思想与文化经济再生产
文化和经济再生产
许多经济学家,而不是少数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历史学家,对学校有着独特的看法。他们设想学校的教育方式像黑匣子一样。一种方法是在学生入学之前先测量投入,然后在“成人”进入劳动力的途中或当成人进入劳动力时对其进行测量。在这种观点下,黑匣子内实际发生的事情(所教的是儿童和教师的具体经历),比投资回报率或更根本地说是再生产的更为全球和宏观经济的考虑更为重要。分工。尽管这些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但也许尤其是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学校被视为黑匣子的本质,处理学校在不平等社会中作为生殖力量的作用时,它们并不能证明这些效果如何在学校内部建立。因此,这些人不够准确,无法解释他们想要描述的文化机构在复制过程中的部分作用。但是,正如我在这里将要论证的那样,需要对这种文化做出解释;但是与这些学者和其他学者所采用的相比,它需要一个不同但通常是互补的取向。
在学校里,精英与大众文化有着独特的结合。作为机构,它们提供了非常有趣的,具有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领域,用于研究社会中文化分布的机制。将学校视为文化分布的机制很重要,因为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指出的那样,增强某些阶级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关键因素是对特定社会的知识保存和生产机构的控制。 因此,用曼海姆的话说,学校和其他文化机构选择,保存和分发的“现实”可能需要具体化,以便可以将其视为特定的“社会建构”,这可能不符合每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利益。
现在,把现实说成是一种社会建构,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学和教育文学中的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这些学者,特别是那些有现象学倾向的学者,意味着两件事。(1) 成为一个人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一个开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人接受一个特定的社会现实作为现实来宣扬,就像生活“真实存在”的方式一样。(2)在更大的范围内,维系和组织一个集体的社会意义是由人们在前进过程中不断的常识性互动模式所创造的关于他们的生活。现在,将社会因素重新引入到盎格鲁-西方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心理问题中,这无疑是对许多教育者观点的一种改进,他们认为,人们用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并试图通过其文化机构传递的意义模式独立于社会或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现实的社会建构”这一概念有点过于笼统,在理解文化机构,特别是学校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形式的总体框架和结构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帮助,正如怀蒂简洁说的那样。
过分强调现实是社会建构的概念似乎导致人们忽略了对现实如何以及为什么以特定方式来建构,以及现实的特定建构似乎如何以及为什么具有抵制颠覆的力量的思考。
因此,现实社会建构的一般原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社会和文化意义而不是其他意义是通过学校分配的;它也没有解释对知识保存和生产机构的控制如何与社会集体中强大群体的意识形态统治联系起来。
相反的原则,即知识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和控制没有任何显着关系,这当然也是有问题的,尽管这可能使许多课程理论家感到惊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对文化的社会分布进行批判性分析时,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人们一生所遵循的意义和价值观模式,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被看作是自主的,并在其自身的范围内不断演变,但最终将这一模式与精确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分离是非常不现实的,它可以将其影响扩展到感觉和行为中最意想不到的区域。作为变革的关键,教育的共同处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是由(政治)决定和(经济)维持的实际制度所影响的,在某些情况下是由这些制度所决定的。
Whitty和Williams都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和学校知识之间的关系的相当棘手的问题,但背景一般是英国的。我们不应感到惊讶的是,欧洲大陆和英国在处理文化与控制之间关系问题方面有着相当广泛的历史。一方面,他们的阶级对立比美国要少一些。美国教育和文化学术界对意识形态分析的传统不太清楚,这说明了另外两个问题,即大多数教育活动的非历史性和通过技术模式改善的伦理的主导性在大多数课程论述中,课程领域的非历史性在这里相当有趣。任何熟悉进步教育协会在其历史上内部和边缘的激烈争论的人很快就会意识到,进步教育者之间的主要争论点之一是灌输问题。学校是否应该在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的指导下,向学生传授一套特定的社会意义?他们是否应该只关注进步的教育技术,而不是支持某一特定的社会和经济事业?这种类型的问题在过去一直困扰着民主思想的教育工作者,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词汇不同。
事实上,正如进步教育协会的早期组织者之一斯坦伍德·科布所说,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许多进步教育工作者甚至对提出学校应该教授和评估哪些实际内容的问题相当谨慎。他们往往倾向于主要关注教学方法,部分原因是课程的确定被认为是一个政治问题,可能会分裂运动。科布对这些教育者选择活动场所背后更大的结构性原因的估计可能是历史上准确的,也可能不是。但事实仍然是,至少在现象学上,许多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学校和其他机构保存和传播的文化并不一定是中立的。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往往源于这种认识。不幸的是,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些反复出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并没有像在英国和法国那样影响到美国当前的课程论证。然而,正如我们也看到的那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像我们这样的先进工业社会的学校可能为某些社会阶层服务得相当好,而其他阶层则根本不太好。因此,我认为没有什么领域的调查比试图揭示我们文化机构的意义和控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迫。
虽然我现在还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文化和控制理论(尽管像雷蒙德·威廉姆斯、皮埃尔·布迪厄和巴兹尔·伯恩斯坦这样的人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但我想在这里做一些事情。首先,我想对最近关于意识形态和学校经验之间关系的工作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框架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这将与当今课程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相比较。然后,我将从课程与思想经济结构之间联系的一个方面来论述,并概述一些关于课程与思想经济结构之间联系的一般性命题。这些命题应该更多地被视为假设,而不是最终的证明,毫无疑问,需要历史、概念和经验,更不用说比较研究来证明其成果。这些假设将涉及课程知识在我们社会中的高地位与其经济和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如果不试图揭示将文化和经济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复杂关系,就很难思考课程形式和内容的过去和现在的问题。让我们从布里弗利开始,把现存的传统看作是理想的类型,这些类型往往为当前的课程工作提供假设性的背景。
成就与社会化传统
今天,很大一部分教育、课程理论和学术都是从现有的各种学习心理中获得纲领性动力和逻辑性依据的。虽然施瓦布和其他人已经证明,试图从学习理论中导出课程(或教育学)理论是一个逻辑错误,但太多的课程理论家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还有另一个困难与我在这里的讨论更为密切。正如我稍后将更充分地说明的那样,学习的语言往往是非政治性的和非历史性的,因此隐藏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与资源之间的复杂联系,而这些关系是在相当多的课程组织和选择背后的。简言之,它并不是一个足够的语言工具来处理关于学校知识的一些可能的思想根源的课程问题。从最简单的方面来说,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学校到底教什么?“学校传授的知识有哪些明显和潜在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用来计划、排序和评价这种知识在阶级关系的文化和经济再生产中的作用的选择和组织原则如何?“这些问题通常不是心理学语言游戏的一部分。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概念框架,这是一个棋盘,在这个棋盘上,这种类型的语言游戏可以玩得更远一些。
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学校知识的调查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是围绕学术成果问题,第二个问题与学校作为社会化机制的作用相比,更不关心成就问题。
在学业成就模式中,课程知识本身并不成问题。相反,进入学校的知识通常被认为是给定的、中立的,这样就可以在社会群体、学校、儿童等之间进行比较,因此,学习成绩、差异性,基于未经检验的、被解释为有价值知识的前提的分层是研究背后的指导性兴趣。重点往往是确定对个人或群体在学校的成败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例如“青少年亚文化”、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或者说,学生的社会背景。社会目标是最大化学术生产力。
与学业成就模式不同,社会化方法并不一定让学校知识未经审查。事实上,它的主要兴趣之一是探索学校所教授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然而,由于这种兴趣,它将自己局限于所谓的“道德知识”的研究,它确立了给定的社会价值观,并探讨学校作为社会的代理人如何将学生社会化为其“共享”的一套规范规则和处置。罗伯特德雷本的著名的小书,关于什么是在学校学到的,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
当然,这些方法并非完全错误,过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学校是文化和社会机制,尽管也许并非总是以预期的方式。事实上,德雷本和其他人对社会化的扩展描述的一个优点是,它们增强了我们阐明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的能力,因为这种方法实际上被认为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它们超越了自身,指向了学校。他们心照不宣地接受,因此,没有提出质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仔细观察,这两种研究传统各有各的问题。学术成就模式越来越强烈地受到管理层对技术控制和效率的关注,已经开始忽视知识本身的实际内容,因此除了争论,比如说,如果要保持民主,就必须“生产”纪律性很强的学生,等等。社会化传统虽然以自己的方式具有深刻的见解,但它侧重于社会共识以及更大集体的“既定”价值观与教育机构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种社会价值发挥作用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以及某些社会价值成为(根据谁的定义?)此外,两者几乎完全忽视了学校课程形式和内容的某些潜在功能。这正是所谓“学校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所要探讨的问题。
学校知识的社会学与经济学
第三个也是更具批判性的传统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杨在他的论点中阐明了“获得权力与使某些主要类别合法化的机会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以及这些类别对某些群体的可用性使他们能够主张权力并控制其他群体的过程。”因此,换言之,问题涉及到如何通过文化的“传播”来维持和部分重建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体系,显然,作为文化和经济再生产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代理人(毕竟,每个孩子都会去,作为认证和社会化机构,它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在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机构。
与社会化传统一样,这些研究的焦点一直是一个社会如何自我稳定。学校在维持经济和教育产品和服务的控制、生产和分配方式方面有何地位?然而,这些问题是由一种比德雷本更为批判性的姿态引导的。因为这些人对这类特殊问题的承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和。它们以类似于我在第一章中所采取的立场开始。这大体上类似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即,一个社会要真正公正,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最不得利者的优势。因此,任何在控制和获得文化和经济“资本”(例如,最近的经济报告显示,我们的资本)方面增加贫富之间相对差距的社会都需要受到质疑。如何使这种不平等合法化?为什么被接受?正如葛兰西所说,这种霸权是如何维持的?
对这些研究人员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看似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稳定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依赖于个人所遵循的原则的深层的、往往是无意识的内化”现有的社会秩序。然而,这些原则并不被认为是中立的。它们被视为与经济和政治层面密切相关。
例如,在Bowles和Gintis、Bernstein、Young和Bourdieu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分析中,个人对他或她所参与的社会秩序的潜在感知提供了理解的源泉。举一个例子,用一位英国评论员对鲍尔斯和金蒂斯有趣但过于机械化的书的话来说,“在鲍尔斯和金蒂斯的作品中,强调了学校教育在形成不同的人格类型方面的重要性,这些人格类型符合经济模式下工作关系体系的要求这样一来,对于鲍尔斯和金蒂斯来说,教育不仅将个人分配到社会中相对固定的一系列职位,由经济和政治力量决定的职位分配,而且教育过程本身,正式的和隐藏的课程,使人们社会化,接受有限的他们最终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其他类似取向的学者在研究学校可能对个人意识形成的影响时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因此,例如,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个人的lsquo;心理结构rsquo;(即思想、语言和行为的类别)得以形成,这些心理结构源自社会分工。”在法国,布迪厄正在对文化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行调查。他分析了把经济和文化控制和分配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规则,他称之为习惯。
布迪厄关注的是学生应对所谓“中产阶级文化”的能力。他认为,储存在学校中的文化资本在等级社会的再生产中起着有效的过滤作用。例如,学校通过看似中立的选择和指导过程,部分地重建了更大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等级制度。他们把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即惯习,视为自然,并把它当作所有儿童都能平等地使用它。然而,“通过平等对待所有儿童,同时含蓄地偏爱那些已经具备处理中产阶级文化的语言和社会能力的人,学校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礼物的东西,即文化资本视为自然。”布迪厄因此要求我们把文化资本视为经济资本。正如我们的主要经济机构的结构是为了让那些继承或已经拥有经济资本的人做得更好一样,文化资本也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文化资本(“好品味”,某些先验知识、能力和语言形式)在整个社会中分布不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分工和权力。“通过选择这些财产,学校有助于在社会中再现权力的分配。”对于布迪厄来说,要完全理解学校做什么,谁成功谁失败,就不能把文化看作是中立的,因为文化必然有助于社会进步。相反,人们认为学校里默认的文化是导致这些机构之外不平等的原因。
因此,在这些观点的背后,有一种论点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与贫穷一样,成绩不佳不是一种反常现象。贫困和诸如低成就等课程问题都是我们所知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组织的不可分割的产物。当我们在本分析的下一节中进一步考虑学校知识的正式语料库时,我将有更多的话要说,很快就会看到许多课程问题,例如成就,是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40181],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