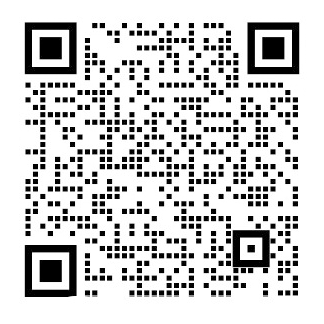政策支持和中国农村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外文翻译资料
2021-12-17 22:05:33
政策支持和中国农村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邓衡山,黄季焜,许志刚,斯科特·罗泽尔。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
斯坦福大学斯普利研究所;斯坦福,加利福尼亚,美国
中国大多数农场规模较小,容易受到强大市场力量的冲击。认识到面对小农经济的挑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对其产生和发展进行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况、近期政策措施的性质及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在推动近期趋势方面发挥了作用。基于一个独特的面板数据从两轮2003年和2009年对全国380个村庄的代表性调查表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几乎没有农村人口流动人口,21%的农村人口有农村人口流动人口2008年,为2400万农户提供服务。FPC的行列式分析表明,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政策支持2006年《金融交易法》通过后,中国采取的措施,很可能还有新的法律环境,占fpc增长的大部分。
1. 介绍
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农业领域通过实施家庭联产责任制,这项改革将集体所有(或村控制)的土地平均分配给个人、每个村庄的家庭。家庭拥有15年的土地使用权。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土地使用合同被续签,再过30年,在2008年,中国领导人宣布这些用户权利将无限期有效(国务院2008)。
以往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源管理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早期改革时期(1978-1984)。从1978年到1984年,粮食生产的年增长率接近5%。(2004 - 2009)。经济作物的产量增长更快(例如,油料作物每年增长14.9%;棉19.3%;肉类产量每年增长9.1% (NSBC, 2004-2009),生产率提高和农产品价格上涨。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农村贫困水平。1978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150%,和1984年相比,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1984年的14.8% (NSBC, 2007),人力资源管理也促进了中国市场的发展,改革后期(1984年以后)的扩张。中国农村的发展帮助许多农民种植和销售,基于市场价格的决策,导致许多农民转向生产更高价值的作物(Huang amp; Rozelle,2006)。早期,中国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占了绝大部分,改革时期(McMillan, Whalley,amp; Zhu, 1989;林1992;黄,罗泽尔,1996;Fan1997)。
表1
农民专业合作社(FPCs)的出现和中国平均农场规模,1984-2008。
资料来源:FPC数据来自作者2003年和2009年的两轮调查。平均农场规模数字来自NSBC,从1986年到2008年的各种问题
fpc村庄平均农场规模的年百分比 在中国
基于2003年和2009年调查的380个村庄,基于2003年调查的全部样本(2459个村庄)
2004-2008年的数据是基于2009年第二轮调查。与2003年相比,2004年和2005年的数字可能略有下降
对村长在过去可能忘记FPC活动的错误召回。
虽然人事制度对我国农业在改革初期的突出表现做出了贡献和促进,在随后的许多经济改革中,中国人口组织的性质,事实上,创造了一系列的挑战.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负责将农业转变为现代产业的人。鉴于农村人口众多(超过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有8亿人口,约2亿户),中国的平均农场规模仅为8亿,1984年约0.73公顷(表1)。随着农村家庭数量的增加,改革前25年的平均农场规模实际上有所下降。到2003年,每个农村家庭平均只有0.54公顷土地用于种植农作物。尽管平均水平略有上升,每个农场的规模(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都是由农户之间的耕地租赁交易决定的.随着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2008年平均农场面积仍只有0.6公顷(表1)。此外,本世纪初中国典型的农场生产资产价值不足700美元(合人民币5600元,2006)。如今,中国大多数农场都是小型劳动密集型单位,容易受到强大市场力量的冲击。
在国际上,尽管关于农民合作社和农业发展的文献存在着积极的争论(例如,Staatz, 1987),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合作安排对新兴市场起着重要作用。当生产系统是原子化的,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往往很差,这可能会限制农户的收入收入可能性(Mendoza amp; Rosegrant, 1995)。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合作社有被证明能够帮助农户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投入,销售其产出并提高生产效率(Fulton, 1995;lele,1981)。
对文献的回顾也表明,重要的是要安排适当的机构或体制框架促进农民合作社(Ostrom, 1990;Stefanson, 1999)。通常需要鼓励或鼓励农民加入这样的组织,但要成为成功的农民合作社也必须是自愿的(哈里斯,斯蒂芬森,amp;富尔顿,1996;Coolt.1994)。世界各地的政府(或政府的某些代理人)经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合作社(富尔顿,2005)。例如,在美国,支持合作社的工作是推广服务的一些代理人的工作。在日本有一个特别的部级合作委员会。欧洲的合作社运动相当成熟,而且是地方性的合作社是由上层的泛国家合作协会(往往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非正式网络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在中国,政府(特别是农业部级制度)负责促进和培育全国农民合作社。.认识到发展分散化农业的挑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生产和销售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推动了不同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在理论上,推广举措强调了农民参与的自愿性,政府承担了农民自愿参与的角色,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主要催化剂。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政府官员直接参与了建立农民合作社。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区的官员采取了额外措施来促进农业投入供应合作社或专业生产技术协会。地方政府提供了财政支持支持合作社援助(Han, 2007)。近年来,法律改革和援助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出现。
那么,中国农业合作社的现状如何呢?有一些问题已经提出了关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状、政策环境及政府行为的作用。具体来说,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如何?农民怎么了解专业合作社功能?他们为会员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人们正在做着多么大的努力?政府促进农民合作社?这些措施对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出现有什么作用?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中国农村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农村政策,近年来(国务院,2009),此类机构的知名度仍然相对较低。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报道。其产生和发展是基于从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样本中仔细收集的实地调查数据。由于缺乏资料,很难回答上面一段提出的问题。农业方面称,2008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达到18万家(MOA, 2009)。相同的有消息称,9.7%的农民至少属于一个农民专业合作,这意味着中国有2460万农民合作社成员。袁(2008)说(没有文件/来源)有150个。100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3500万人(占农户总数的13.8%)。这些是数字准确吗?这些数字的来源通常不清楚。在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论研究文献中,大部分的论文/文章都是基于个案研究或小规模的地方调查(例如,孔果,2006;黄,傅,黄,1999;汉族,2007;徐,黄,2009;赵,2009)。这些研究很少寻求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趋势。除了沈,罗泽尔和张(2005)和韩(2007),没有研究试图估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轨迹。沈等人(2005)报告了来自六个国家的数据收集工作。数据显示,到2003年,中国约有10%的农村拥有农民专业协会,而2003年几乎没有,1990年代早期,Han(2007)估计,农民专业协会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到2004年,中国约有22%的村庄成立了农民专业协会。
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回答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的一些基本的突出问题。更准确地说,我们感兴趣的是描述农民合作社的出现和现状,最近政策倡议的性质和政府政策在促进最近趋势方面发挥了作用。
为了实现这些总体目标,本文组织如下。在下一节中,我们的抽样程序,数据描述了作者的收集工作和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范围。然后我们将追溯并举例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本节还记录了最近涉及的策略更改农民专业合作社。第4节提供了关于最近两者之间关系的描述性/相关性分析,政府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倡议及其出现。第5节寻求更正式的分析,同样的问题,通过指定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并给出多元分析的结果,最后一节总结。
研究不断变化的机构,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必然需要仔细的定义和意愿,涉及某些局限性。例如,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组织—专业的和其他的中国农村。在本文中,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限制在参与农业生产的农民组织上(产生工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洪水;等等)。今天的FPC不同于公社,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旅曾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中国的FPC更像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合作,包括提供投入、管理生产和推广技术的组织以及那些主要从事市场营销的公司)。中国的合作组织有不同的名称缩写词。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本文的其余部分使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FPCs)这个术语。
2.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两轮全国调查收集的数据子集。作者在2003年末(主要收集2003年的数据)和2009年初(主要收集2008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在开展第一轮调查之前,我们设计了一个以该村为基本单元的抽样程序分析。我们选择了样本,并在6个省和36个县进行了调查,几乎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样本。4样本省份均随机选取自我国各主要农业生态区。样本村庄的选择是由调查小组在每个样本省份统一实施的过程。
每个省选出6个县,从按总量降序排列的县列表的每一列中选出2个县,人均工业产值(GVIO/capita)。GVIO/capita是根据Rozelle(1996)中GVIO的调查结果使用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潜力的最佳预测指标之一,往往使其更可靠(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超过农村人均纯收入(虽然与人均收入高度相关;之间的相关系数。人均GVIO和农村人均收入均高于0.75)。在每个县内,我们还选择了六个乡镇程序为县选。当我们的统计小组访问216个乡镇(6个省times;6个县times;6个镇乡)官员要求每个村派两名代表(通常是村长和会计)参加一个会议。普查人员平均在每个乡镇调查了大约11个村庄,调查了2459个村庄。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主要使用了针对fpc的调查数据。在回答了有关经济和政治的问题以及他们村庄1997年和2002年的人口状况,我们也询问了受访者他们村子里是否有农民属于FPC。被调查者被要求将参与分配给已经建立的FPC的成员,在他们的村子里,以及那些在村子边界外属于FPC的人。如果答案是“是的,有一个FPC。受访者回答了一组关于FPCs活动的问题。调查问卷是旨在收集有关该协会规模、覆盖范围、主要职能和章程的信息,注册规则和内部组织。调查还包括一个子块,试图了解如何的行动,政府机构影响金融中心的开办和运作。
在2009年的调查中,我们在380个村庄进行了第二轮的数据收集,所有这些村庄都是从2003年调查的2459个村庄。我们缩小了村庄样本的规模,因为在第二轮我们希望在重复村长调查的基础上,对FPC管理人员进行深入访谈。以确保第二次调查也将具有全国代表性,我们遵循了精心挑选的村庄子样本包括在内。首先,我们淘汰了甘肃省,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代表西北的省(陕西),中国在调查的5个省中,我们随机从每个县中选取一个县(有3个县,6个县2003年调查的各县)。在每个选定的县内,我们将6个样本镇(从2003年开始)分成两组(一组包括最贫穷的三个城镇,另一组包括不贫穷的三个城镇)。然后我们随机选择一个,来自两个镇的团体。和之前一样,在选定的城镇中,我们包括了城镇中的所有村庄(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全镇所有村庄FPC活动普查)。2009年第二轮调查共覆盖5个省份,15个县、三十个乡、380个村。
在完成对村长的调查之后(在调查期间我们收集了关于村庄和他们的一般信息),我们约见了在所有380个拥有固定资产管理权的村庄的每一个固定资产管理权的管理人员。我们一共采访了112位FPCs的经理。问卷调查的重点是收集有关的基本信息:FPC的成立,其管理性质、治理、业务实践以及各种其他问题FPC活动及其与政府政策支持措施的相互作用。
3.FPC的演变与中国的政策环境
在本节中,我们记录了近三十年来FPC出现的最新趋势,并描述了其中的一些FPC为其成员提供的服务。虽然样本量相对较小(2003年仅占全国农村的0.38%),在假设我们的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情况下,使用区域村庄数量作为统计权重(正如我们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估计(通过从我们的样本外推到(中国其他地区)全国FPC点估算和趋势。
中国FPCs出现的结果见表1第1列和表2。第一列是估计值到2008年FPC的数量。这些数字基于我们对380个村庄的面板数据(2009年的调查)的数字。第二列是根据2003年收集的全部样本(即2459个村庄的调查)按日期引用的。比较第1和第2列,来自较小样本(2009年收集的)的数据似乎略微低估了,所有年份都有fpc的村庄(与较大的2003年样本相比)。两种趋势在水平上的差异.从我们的两次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不应掩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两组估计数据得出的总体趋势(估计结果是相隔5年得出的)相似之处可能让人相信,这些估计结果是相对一致的。
表1显示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从我们的调查中得出的趋势与国家政策的演变是一致的。最痛苦的是,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FPC从未发生。根据数据集(2003年和2009年的数据集),FPC在早期和中期增长缓慢,改革年(1980年代和1990年代)。例如,根据2003年的调查,在1987年农村人口普查出现
Policy support and emerging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rural China
Hengshan DENGa,b, Jikun HUANGa,⁎, Zhigang XU a , Scott ROZELLE c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Jia 11 Datun Road, Anwai, Beijing 100101, China .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East Encina Hall; Stanford, CA 94305, USA
ABSTRACT
Most farms in China are small and vulnerable to the forces of powerful markets. Recognizing the challenges of small farming, China has promoted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FPC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overall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emergence and current status of FPCs, the nature of recent policy initiative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have played in promoting recent trends. Based on a unique panel data from two rounds of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urveys of 380 villages in 2003 and 2009, this paper shows that while there was nearly no FPC in late 1990s, there were FPCs in 21% of China#39;s villages and these FPCs provided services to about 24 million farm households in 2008. The determinants of FPC analysis show that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Policy support measures and, most likely, the new legal setting in China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2006 FPC law,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growth of FPCs. copy; 2010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ntroduction
China#39;s economic reform from 1978 to 1984 was initiated within its agricultural sector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HRS). This reform equally allocated collectively owned (or village-controlled) land to individual households in each village. Households had land-use rights for 15 years. In the mid-1990s land-use contracts were renewed for another 30 years and in 2008 China#39;s leadership announced that these user rights would be indefinitely valid (State Council, 2008).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HR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hina#39;s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increased farmer income in the early reform period (1978–1984).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grain production was nearly 5% between 1978 and 1984 (NSBC, 2004–2009). The production of cash crops increased even more quickly (e.g., oil crops grew by 14.9% annually; cotton by 19.3% annually), and meat production grew by 9.1% annually (NSBC, 2004–2009).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and rising agricultural prices led to improved farmer income and reduced levels of rural poverty. Per capita income in real terms increased 150% between 1978 and 1984. The incidence of rural poverty fell from 30.7% in 1978 to 14.8% in 1984 (NSBC, 2007). HRS also facilitated China#39;s market expansion in the later reform periods (after 1984). China#39;s rural developments helped many farmers make planting and marketing decisions based upon market prices, which led many farmers shift into the production of higher valued crops (Huang amp; Rozelle, 2006). Productivity gains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rural China contributed to the majority of economic progress during the early reform period (McMillan, Whalley, amp; Zhu, 1989; Lin 1992; Huang amp; Rozelle, 1996; Fan 1997).
Although HRS contributed to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China#39;s agriculture in the early reform period and facilitated many of the subsequent economic reforms, the nature of China#39;s demographic organization, in fact, created a set of challenges to those charged with transforming agriculture into a modern sector in the 1980s. Given the large rural population (more than 800 million in the early 1980s residing in approximately 200 million households), the average size of a farm in China was only about 0.73 ha in 1984 (Table 1). With rising rural households, the average farm size actually fell during the first 25 years of reform. By 2003 each rural family, on average, had only 0.54 ha on which to grow crops.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a slight rise in the average size of each farm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1950s) due to cultivated land rental transactions among farm households, which has accompanied the large shift of labor into the off farm sector, the average farm size was still only 0.6 ha in 2008 (Table 1). Furthermore, the typical farm in the early 2000s in China had productive assets valued at less than US$700, or 5600 yuan (Rozelle amp; Huang, 2006). Today, most farms in China are small, labor-intensive units that are vulnerable to the forces of powerful markets. Internationally, although there are active debates in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farmer cooperative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g., Staatz, 1987), most development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cooperative arrangem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emerging economies. When production systems are atomistic, infra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networks tend to be poor, which can limit the income earning possibilities of farming households (Mendoza amp; Rosegrant, 1995).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cooperatives have been shown to help farm households access inputs at lower prices, sell their output and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Fulton, 1995; Lele, 1981).1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lso shows that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right agency or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be arranged to promote farmer cooperatives (Ostrom, 1990; Stefanson, 1999). Often farmers need to be encouraged or enticed to join such organizations, but to be successful farmer cooperatives must also be voluntary (Harris, Stefanson, amp; Fulton, 1996; Cook, 1994). Around the world governments (or some agent of the government) often are involved with cooperatives in one way or another (Fulton, 2005). For example, in the US it is the job of some agents in the extension service to support the work of cooperatives. In Japan there is a special ministry-level
资料编号:[4734]
课题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