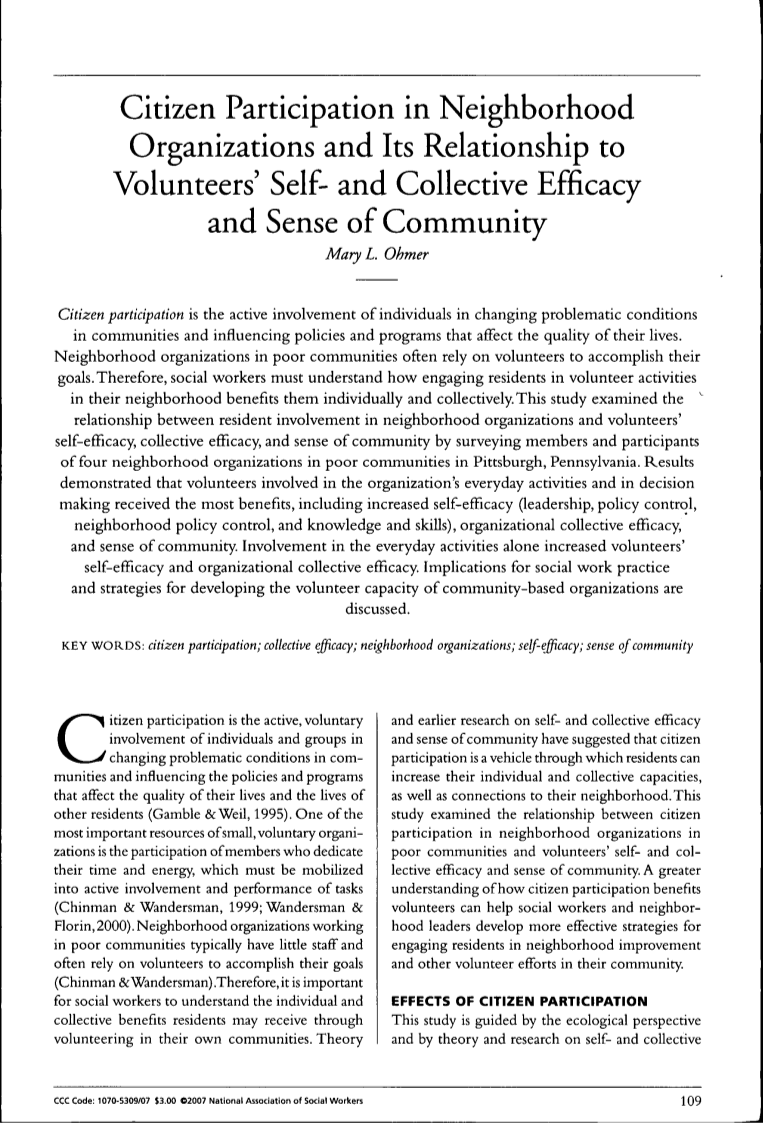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3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社区组织中居民参与及其与志愿者自我效能、
集体效能感和社区意识的关系
摘要
居民参与是个人积极参与,也是社区中多变的不确定的因素,并且影响着事关其生活质量的政策与计划。贫困社区的邻里组织往往依靠志愿者完成他们的目标,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了解社区居民在社区志愿活动中如何使个人和集体受益。本研究通过对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四个贫困社区的社区组织成员和参与者的调查,考察了居民参与社区组织与志愿者自我效能感、集体效能感、社区感的关系。结果表明志愿者参与了组织的日常活动和最大利益决策,包括提高自我效能感(领导力,政策控制),邻里政策控制,知识与技能,组织集体效能,及社区意识。单独参与日常活动增加了志愿者的自我效能感和组织集体效能感。同时本文讨论了社会工作实践的含义和发展社区组织志愿者能力的策略。
关键词:居民参与;集体效能;邻里组织;自我效能感;社区意识
居民参与是个人和群体积极、自愿参与的过程,也是社区中多变的不确定的因素,并且影响着事关他们及其他参与者生活质量的政策与计划。(Goable amp; WIL,1995)中积极主动的参与。一些成员被动员成为积极参与和履行任务的人,而这些致力于投入时间和精力的成员的参与是小型志愿组织最重要的资源之一(Chinman amp; Wandersman, 1999; Wandersman amp; Florin, 2000)。在贫困社区工作的社区组织通常很少有工作人员,常常依靠志愿者来完成他们的目标(Chinman amp; Wandersman)。因此,对于社会工作者很重要的是,了解志愿者可以通过社区里的志愿活动获得的个人和集体利益。个人和集体效能和社区意识的早期理论和研究表明,公民参与是一种工具,通过它,居民可以增加他们的个人和集体能力,以及连接到他们的邻里。本研究考察了贫困社区邻里组织公民参与与志愿者自我效能感、集体效能感和社区意识的关系。以及通过进一步地了解公民参与如何使志愿者受益,来帮助社会工作者和社区领袖制定更有效的策略,使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及改善其他志愿工作。
居民参与效应
本研究以生态视角为指导,以对自我效能感、集体效能感和集体意识的理论研究为导向。Pinderhughes(1983)使用了一个生态框架,认为生活在贫困社区中的个人的无力感,只能通过影响外部社会系统以减少破坏力并联合如教堂、企业或学校等家庭外部系统协作的策略来解决,以此来改善他们的环境。公民参与是一种手段,居民可以影响外部社会制度,并与邻里和社区组织共同改善他们的社区。自我效能感、集体效能感和集体感的理论与研究阐明了公民参与是如何通过促进他们的个人和集体能力以及与他们社区的联系来帮助志愿者的。
自我效能感
Bandura(1982)将自我效能描述为个体对自己组织和执行实现所需目标所必需的行动的能力的自我判断。那些对自己的能力有强烈信念的居民会接近应激源,因为他们确保能够对其进行一些控制,包括在弱势社区经常发现的问题(Bandura,1989)。研究表明,积极参与的居民改善社区的努力与增强自我效能感和授权感有关。在对以色列居民活动的研究中,Itzhaky and York(2000)发现有组织的参与有助于参与者对个人和社区决策的控制感,参与决策有助于服务控制,以及居民代表的参与有助于个人赋权(被定义为对个人和社区的决策和对子女和家庭的服务的控制感)。在纵向研究中,Itzhaky and York(2002)发现,公民参与会提升居民自尊和对周围环境的掌握(即对环境和未来的控制),以及增加个人赋权和社区赋权(即,了解社区的服务,知道如何改善服务,游说,并保持与政治家的强烈接触)。
社会政治控制指的是在社会和政治系统中对一个人的能力、效能和控制感的信念。(Zimmerman amp; Zahniser,1991)Zimmerman and Rappaport (1988)发现,在不同的社区组织中,学生和社区居民的更多参与与个人政治效能的期望和实际经验有关。(例如,能力和掌握、控制感和公民责任)。在一系列研究中,Zimmerman and Zahniser发现,更多参与志愿组织和社区活动的个人在社会政治控制措施(领导能力和政策控制)上的得分高于那些较少参与的。Itzhaky arid York(2000)发现,公民参与与经验丰富的社区积极分子的更优社会政治控制相关。具体而言,参与水平有助于政策控制和领导能力,参与时的犹豫不决则有助于政策控制。
集体效能感
自我效能理论关注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判断或判断,集体效能理论解释了群体成员对干预邻里问题的能力的信念或判断,以维持社会控制和解决问题(Wandersman amp; Florin, 2000). 集体效能可以被概念化为一个社区和一个组织过程。邻里集体效能被定义为相互信任和社会凝聚力与共同支持邻里社会控制的共同期望的联系(Sampson amp; Raudenbush, 1999). Sampson and Raudenbush争辩说,居民不太可能在人们不信任的社区采取行动,而且规则还不明确。公民参与是一个潜在的机制,促进邻里集体效能,为邻里提供发展信任关系的机会,这为共同的期望和行为创造了基础。Chavis (1987) 发现街区关联成员比非成员更可能有邻域集体效能的期望,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集体工作解决问题,并期望居民干预以维持社会控制。Sampson和他的同事(1997)发现邻里集体效能与组织参与呈正相关,以及友谊和亲属关系和邻里服务。
组织的效力是指组织或团体对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能力的认识,以改善其成员的生活(konis amp;amp;Wenocur,1994)。集体效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集体力量产生预期结果的共同信念(Bandura, 2001)。公民参与可以通过合作解决社区问题,为志愿者提供发展集体解决问题技能的机会,从而影响组织的效果。Perkins和associates(1996)发现,组织的集体效能和公民责任和社区附属关系始终和积极参与基层社区组织的个人和集团层面的分析有关。
社区意识
社区理论描述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以及他们与社区的联系对他们参与当地组织的影响以及对孤立的缓冲感觉的影响(Wandersmanamp;Florin,2000)。McMillian和Chavis(1986)把社区归属感定义为“一种成员有归属感的感觉,一种成员因彼此需求而组成一个共同承诺和信仰的感觉”(p.9)。有几项研究发现,以下类型的参与与更强烈的社区意识有关:参与宗教和社区组织并居住在社区,社区参与和选民登记的比例更高。(Brodsky,0rsquo;campo,amp;Aronson,1999);参与集团协会(Chavis amp;Wandersman,1990;Chavis et al .,1987);参与社区组织和养育孩子(Obst, Smith,amp;Zinkiewicz,2002);参加团体和协会,如体育协会、教区、文化组织、工会和政治和志愿工作协会(Prezza, Amici, Roberti,amp;Tedeschi,2001)。
这一理论和研究证明了公民参与、自我和集体效能以及社区意识之间的联系。然而,只有很少的研究(例如, for example, Brodsky et al,1999; Chavis et al., 1987; Itzhaky amp;York, 2000a,2000b, 2002)调查贫困社区居民志愿服务。另外,将公民参与作为促进集体效能的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本研究通过考察贫困社区社区组织中居民志愿服务与社区的自我和集体效能以及社区意识之间的联系,从而对现有研究做出贡献。在本研究中,公民参与被概念化为志愿者参与组织和参与决策的程度。通过考察居民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效能(社会政治控制)及其在社区发展和解决问题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来衡量自我效能。集体效能包括社区和组织的集体效能。最后,社区意识被定义为一种归属感或与邻居的联系。
方法
这项研究采用了一项跨部门的七步调查,调查了宾夕法尼亚州大都会匹兹堡市四个社区的小型非营利性社区组织的成员和参与者。这四个组织都处于贫困地区,由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定义为人口普查区,其中20%或更多的居民贫穷(Bishaw, 2005)。他们的总体目标是改善有问题的条件,影响关于社区生活质量的政策和项目。所有四个组织都有当地的控制委员会(也就是说,他们是由居民和社区利益相关者组成)和至少50到100个成员的基础。这些组织通过各种社区活动改善社区条件,包括美化环境、社区规划、社会和娱乐活动、社区报纸、经济适用房、商业和经济发展、预防犯罪和安全、青年发展、领导发展和居住街区组织。这四个组织也包含着Hazelwood的倡议,其任务是改善和美化社区(Hazelwood Initiative, Inc.,n.d);家园地区经济振兴公司,其使命是振兴社区;更好行动的街区,其使命是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促进社区的发展和稳定,帮助居民建立必要的技能来克服成功的障碍;中北部的社区委员会,其任务是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北区中央社区委员会,n.d)。在组织会议上,非盟驻地成员和参加组织的参加者被邀请填写一份调查报告,在组织会议上分发,并通过邮件向231人发送。我在组织会议和问卷调查的信中提供了关于该研究的信息,包括对所提议的研究的概述和知情同意的基本要素(即告知参与者该研究是自愿的和机密的),总体反应率是54% (N = 124)。各组织的反应率如下:39%,中北部居委会;51%,Hazelwood倡议;53%,家园地区经济振兴公司;72%,更好行动的街区。最有效的数据收集方法是面对面(76%的响应率),其次是组织会议(62%的响应率),然后是邮件(26%的响应率)。
样本
所有被调查者都是贫困地区的居民(1999年社区贫困率从24%到38%不等)(大学社会与城市研究中心,2002年)。受访者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3人。总体上,8%的受访者年收入在1万美元或不到1万美元,16%的人年收入在10,001美元至2万美元之间。因此,24%的被调查者有贫困或接近贫困的收入(他们的贫困线标准是:2人家庭的12334美元和65岁以上的12971美元(65岁以上),2人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美国人口普查局,2004)。在剩下的受访者中,24%的收入在20,001美元至3.5万美元之间,18%的收入在35,001美元至50,000美元之间,34%的人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
超过一半(59%)的受访者为白人,39%为非裔美国人,2%来自其他种族或族裔群体;62%是女性。几乎都是注册选民(97%)。平均年龄为58岁;41%的受访者年龄超过65岁,这可能有助于解释退休的受访者比例相当大(40%)。大多数受访者是业主(81%);然而,他们的房屋价值相当低,几乎有一半(48%)的人说他们的房子价值在5万美元或更少。受访者都是非常稳定的居民,平均居住在他们的社区34年。几乎一半的人结婚(49%),大多数人接受过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32%的人拥有研究生或专业学位,18%的人拥有大学学位,25%的人拥有大学文凭。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有高中学历(19%)或高中以下学历(6%)。
测量
参与水平 这项措施是根据York(1990)的三项组织参与规模、Perkins和Long的(2002)八项公民参与指数以及Perkins和associates(1990)开发的其他项目进行的。受访者被要求用从“1 =永远5 =通常”表明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参加的11个不同的组织活动的频率,包括参加会议、工作以外的组织会议;组织活动(会议);成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招募新成员(a= .95)。
参与决策 采用Itzhaky和York的(2000a)措施,被调查者被要求通过选择以下6个选项中的一个,来表明他们是如何参与社区组织的:(1)我不参加,(2)我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3)我参与传递信息,(4)我在员工和/或董事会的指导下执行各种任务,(5)我参与了部分计划,决策和执行,(6)我是一个计划、决策和执行的伙伴。
社会政治控制 这些措施包括Zimmerman和Zahniser(1991)的17项社会政治控制量表(衡量领导能力和政策控制)以及为当前研究制定的社区政策控制量表。被调查者被要求指出他们同意的程度,范围从“1 =强烈反对”到“6 =强烈同意”,并陈述关于对他们的领导能力,政策控制,和邻里政策控制的看法。领导能力分量表(8个项目)包括“我更愿意成为领导者而不是跟随者”,“我通常是团队中的领导者”,“我通常可以组织人们完成任务”(a = .73)。政策控制子量表(九项)包括“我觉得我对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重要政治问题有很好的理解”,“我喜欢政治参与,因为我希望尽可能多地参与政府运作,”和“大多数公职人员无论我做什么都不会听我的”(a = .76)。社区控制子量表(七项)包括“我觉得我对我们社区面临的重要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理解,”“我喜欢参与,因为我希望尽可能多地参与社区组织的运作,”以及“对于大多数当地居民,无论我做什么,组织都不会听我的。
lt;
全文共10833字,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6577],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