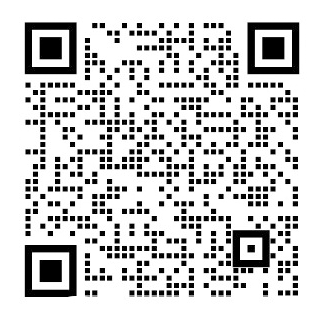共有两篇外文翻译
其一:
Dingxin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is ground-breaking work that explores lsquo;lsquo;overarching patterns of Chinarsquo;s pastrsquo;rsquo;, Zhao Dingxin attempts to address two questions in tandem. First, how and why was China unified and developed into a bureaucratic empire under the state of Qin, after several hundred years of continuous yet inconclusive wars? Second, why, until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political–cultural structure of China that was institutionalized during the Western Han era showed such resilience, despite great changes in demography,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ethnic composition, market relations, religious landscapes, technology, and topography or brought by rebellions or nomadic conquests (Zhao 2015:6)? His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bear the clear mark of Michael Mann, Charles Tilly and possibly other historical comparativists who engage in lsquo;lsquo;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and huge comparisonsrsquo;rsquo; (Tilly 1984). Very briefly, Zhao contends that continuous yet inconclusive wars among states from 770 BC onwards gave rise to instrumental rationalities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fueled a number of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reforms that greatly expanded state capacities. As a result, the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Period wa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onjunctures for state making in Chinese history. At last, the power structure crystallized into the domin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he subordination of ideological power and military power to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economic power, which persisted and continuously shaped and reshaped Chinese history until 1911. This idiosyncratic power structure facilitated and corresponded with a unitary empire (though with short interregnums of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hinging upon Confucian-Legalist ideology. While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was in its embryo during the Warring Period (chapter 4–7), it took shape after Han dynasty (chapter 9). After the Song dynasty, China turned into a Confucian society, where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perfected and local elites were finally suppressed (chapter 12).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vis-a`-vis a Confucian society was so stable that it survived periodical nomadic invasions (chapter 11), the challenges from religions and internal intellectual revolutions (chapter 12), as well as the rise of market economy (chapter 13).
共有两篇外文翻译
其一:
Dingxin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is ground-breaking work that explores lsquo;lsquo;overarching patterns of Chinarsquo;s pastrsquo;rsquo;, Zhao Dingxin attempts to address two questions in tandem. First, how and why was China unified and developed into a bureaucratic empire under the state of Qin, after several hundred years of continuous yet inconclusive wars? Second, why, until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political–cultural structure of China that was institutionalized during the Western Han era showed such resilience, despite great changes in demography,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ethnic composition, market relations, religious landscapes, technology, and topography or brought by rebellions or nomadic conquests (Zhao 2015:6)? His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bear the clear mark of Michael Mann, Charles Tilly and possibly other historical comparativists who engage in lsquo;lsquo;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and huge comparisonsrsquo;rsquo; (Tilly 1984). Very briefly, Zhao contends that continuous yet inconclusive wars among states from 770 BC onwards gave rise to instrumental rationalities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fueled a number of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reforms that greatly expanded state capacities. As a result, the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Period wa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onjunctures for state making in Chinese history. At last, the power structure crystallized into the domin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he subordination of ideological power and military power to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economic power, which persisted and continuously shaped and reshaped Chinese history until 1911. This idiosyncratic power structure facilitated and corresponded with a unitary empire (though with short interregnums of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hinging upon Confucian-Legalist ideology. While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was in its embryo during the Warring Period (chapter 4–7), it took shape after Han dynasty (chapter 9). After the Song dynasty, China turned into a Confucian society, where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perfected and local elites were finally suppressed (chapter 12).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vis-a`-vis a Confucian society was so stable that it survived periodical nomadic invasions (chapter 11), the challenges from religions and internal intellectual revolutions (chapter 12), as well as the rise of market economy (chapter 13).
The book has successfully mastered an ambitious topic that sounds too broad to most of the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sociologists today. It has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in a number of fronts, including Chinese history,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ies, state theory, etc. I will just make two points here. Firstly and methodologically, Zhao argues for the so-called lsquo;lsquo;macrostructure informed, mechanism-based studyrsquo;rsquo; (Zhao 2015:27).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obsession with lsquo;lsquo;mechanismsrsquo;rsquo; had a lot to do with the rise of lsquo;lsquo;middlerange theoriesrsquo;rsquo; originally coined by Merton (1968) during 1960s. At that time, the consolidation of lsquo;lsquo;embedded liberalismrsquo;rsquo; (Ruggie 1982) and the prevalence of positivism urged an empirical turn from macro-theories like that of Parsons to middle-range theories backed by discoveries and tests of mechanisms. However, American scholars soon took for granted the domestic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within which mechanisms work and applied their theories el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共有两篇外文翻译
其一:
Dingxin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赵定新: 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
在这部探索“中国过去总体格局”的开创性作品中,赵定新试图同时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经过几百年的持续而不确定的战争,是如何和为什么统一并发展成为秦国统治下的官僚帝国的?第二,为什么直到19世纪,中国在西汉时期制度化的政治文化结构仍然显示出如此的弹性,尽管人口结构、社会经济结构、民族构成、市场关系、宗教景观、技术和地形发生了巨大变化,或者是由反叛或游牧带来的征服(赵2015:6)?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带有迈克尔·曼、查尔斯·蒂利以及其他可能从事“大结构、大过程和大比较”的历史比较主义者的明显标志(蒂利1984)。非常简单地说,赵辩称,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国家间持续但没有结果的战争导致了政治精英的工具理性,并推动了一些体制和组织改革,大大扩展了国家能力。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关键的建国时期之一。最后,权力结构具体化为政治权力的支配、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对政治权力的从属和经济权力的边缘化,并持续塑造和重塑了中国历史,直至1911年。这种特殊的权力结构促成并与一个单一的帝国(尽管政治分裂的间隔很短)相对应,暗示着儒家法家思想。战国时期,儒家法家国家处于萌芽阶段(第4-7章),汉代以后形成(第9章)。宋朝以后,中国变成了一个儒家社会,官僚制度完善,地方精英最终被压制(第十二章)。儒家法家国家与儒家社会的关系是如此的稳定,以至于它经受住了周期性的游牧入侵(第11章)、宗教和内部思想革命的挑战(第12章)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第13章)。
这本书成功地掌握了一个宏大的主题,听起来太宽泛了,今天大多数的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它已经变得非凡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多个方面的贡献历史研究、国家理论等,我在这里只讲两点。首先和在方法论上,赵主张所谓的“宏观结构知情,基于机制的研究”(赵2015:27)。在社会思想史上科学,对“机制”的痴迷与“中档”的兴起有很大关系“理论”最初由默顿(1968在1960年代创造巩固“嵌入式自由主义”(鲁吉1982)和实证主义促使从帕森斯的宏观理论到中程理论有发现和机制测试的支持。然而,美国学者很快就把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视为理所当然机制在其中起作用并将它们的理论应用到其他地方而没有反应。然而,机制决不是一般的理论;它们是深刻的受时间、空间和结构背景的限制。拿一个最受欢迎的例如政治学的理论。仅在保龄球比赛中,Putnam(2000)就提出20世纪60年代以后电视的普及与女性的职业化自相矛盾地促成了美国公民社会的衰落。虽然它是合理的,如果我们把结构背景从我们转移到北欧国家,同样的机制导致更多的公众参与社会组织的繁荣。不同之处在于政治结构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与专业人员的制度保护妇女(Mahoney和Rueschemeyer,2003年)。
赵对当代社会科学的病态性是非常清楚的。他运用“宏观结构-信息机制基础研究”的方法,将机制重新嵌入到中国古代特有的权力结构中。让我详细说明一下。蒂利(1990)、唐宁(1992)等在西欧经典的战争与国家制定著作中,认为战争的自然选择机制导致了现代国家的统治。然而,赵仔细分析了这一机制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国语境中展开的。例如,虽然胁迫和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对西方的国家建设至关重要,但中国的国家建设只有一条腿,即胁迫而不是资本,因为中国古代的贸易网络和城市如果不是完全不发达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当欧洲发展成为一个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时,中国统一成为一个拥有巨大领土的庞大而有效的帝国;当欧洲的国家建设进程以不同权力基础的精英之间的争斗为特征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从中占了上风刚开始并继续主导其他社会群体。
其次,赵的工作也极大地丰富了国家建设的学术成果。以前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含蓄的,但基本上都没有阐明确切的含义现代国家建设与若干平行历史的关系运动,例如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精英加入国家政治纲领的共同选择代议制民主的兴起。他们的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理论与这些宏观过程中的一个或几个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只代表一条特定的国家建设道路。不过,赵的书,检查上面列出的所有三个进程缺席。首先,正如赵所正确解释的,只有市场经济而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和商人。第二,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工业主义和“高级文化”(Gellner 1983),国家建筑中国古代的历史大多是在没有文化资源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家建设。相比之下,国家建设和国家建设
在西方语境中相互影响。最后,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似乎很多与欧洲相比更加同质化和未分化
罗马帝国的没落和长期的封建制度造成了高度的分裂精英结构。因此,中国政治几乎没有政治竞争的空间代议制民主的前景暗淡。在一起,当年,一群同质的、无与伦比的政治精英来到中国建立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的缺失与现代人类集体主义形式的统一以儒家法家思想为指导,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帝国可能是历史上的“不可避免的事故”。赵的作品,与众多其他带来了非西方国家建设经验的例子国家建设道路的多样性(King and Lieberman 2009)国家建设的多重路径(金和利伯曼2009
尽管它的方法论贡献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叙述对于治国之道,赵的工作也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然而,儒家法家国家却饱受结构还原论的困扰。赵无疑恢复了第一波具有宏观结构的历史比较研究分享他们各种各样的决定论,以及没有认真介绍分析“代理”。第三部分春秋战国时期通过关注政治精英的理性选择,变得更加“机构敏感”,而第四部分则是关于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和持续的基本权力结构的再生产。我们不禁要问:特工们在微观层面上获得或失去能量?他们的兴趣、计算和策略?他们如何决定是服从还是反抗?他们的世界观和论述是什么?相比之下,蒂莉在许多场合被指控为结构主义,他的国家形成理论是以独立的有争议政治理论为补充(Tilly等人。2009年),因此,结构和机构的结合,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赵氏然而,理论框架允许的代理却少得多。
此外,赵同样没有注意到历史。事实上,作为赵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迈克尔曼通过提出权力的间质性根源,与赵的变化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按照他的概念,权力结构总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权力精英将不断重组(曼恩1986)。换句话说,赵仅适用于曼恩理论的前半部分,即社会力量的四个来源,而有意或无意忽略下半部分,即关于变化和重组。在赵的书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权力结构僵化的再现历史。但许多历史著作已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周期性恢复统一的儒家法家国家优先政治权力历史的偶然性比不可避免的命运。事实上,中国历史一直充满了异质性和变革的机会之窗。他们不可能只是简单的解释。它们形成了像暗流一样流动的另类传统时不时地重新露面。更好的结构形成理论结构转型要坚持不懈地应对
其二:
Confucius on Management: 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rial Practices
孔子论管理:理解中国文化价值观管理实践
摘要
孔子经常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个老师”,他制定了标准和价值观仍然渗透着中国文化。尽管中国官方对此不屑一顾自从共产主义革命以来,孔子和他的学说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中国文化基础和管理实践。孔子最近在中国经历了流行的重生,但这种新生的兴趣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挑战。与儒家原则再一次公开本文阐述了孔子的教学思想,并阐述了孔子是如何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这位伟大圣人的古话影响了今天的价值观和实践中国管理。介绍伟大的哲学家和老师孔子生于耶稣诞生前500年,建立了中国的文化基础。他通常被称为“中国第一”并在他的一生中吸引了大批学生追随。孔子的建议然而,在这位伟大的老师死后不久,他以口述的形式给了他的学生学生们开始写他给他们的信息,这些文字成为了《论语》或《孔子语录》(埃姆斯和罗蒙特1998)。虽然许多其他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包括老子而孙子,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管理实践可以追溯到孔子及其价值体系。这是一个强调努力工作、忠诚、奉献、学习的重要性社会秩序。千百年来,直到帝制在中国的覆灭20世纪初,中国的孩子们在学校里会举手向孔子致敬开学日的开始。孩子们会一直背诵孔子的名言被永久地记录在记忆中。随着帝国制度的衰落在中国,儒家学说被消灭;然而,理想是拥护的孔子的《永不离开中国人民》(邢1995;Lin和Chi 2007)。如上所述,斯宾塞(2005),“尽管中国的变化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但它仍然回响着它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文化中,中国人仍然固守着他们悠久的过去深受重要历史人物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为了真正了解另一种文化,有必要探索该文化价值的来源。这中国文化尤其如此。正如Wong(2005)所提出的,管理研究人员未能认识到历史在解释历史的重要性中国人的管理方式。对一种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当一个人探索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历史渊源时组成的文化。就中国而言,我们必须调查hellip;的重要性孔子。虽然儒家思想在官方上受到了毛的质疑,但它的文化价值孔子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最近,儒家思想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教育体系(穆尼2007;并建立了一些孔子学院。中国最近的一本畅销书是文化教授于丹的书北京师范大学的媒体,他们用基本的术语来解释儒家教学(麦格雷戈2007)。儒家价值观要求个人首先尊重自己的职责家庭和社会。个人不像集体那么重要。个人需求为了实现这个群体的需求而牺牲。每个人对家庭都有责任社会取代了对自己的责任。这些值帮助形成了a解放军的管理心态当一个人描述中国人的管理方式时,更多的是通常提到的特征包括集体主义、和谐、集中控制,专制和家长式的领导,家族企业,期望努力工作的员工,强大的组织网络和业务联系。这些特点在中国和海外的华人中都有体现,这些实践可以追溯到孔子所倡导的价值体系。这些儒家的五种关系,五德,和儒家的工作伦理。这五种关系决定了适当的行为和角色组织成员;这五种美德为社会提供了道德框架强调和谐的重要性;而儒家的工作伦理强调的是重要的勤奋、忠诚、敬业、节俭、热爱学习。五个关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到人际关系。适当的行为是由儒家思想决定的上级、父母、丈夫/妻子、长辈和朋友。孔子非常关心人际关系和社会进步当一个人描述中国人的管理方式时,更多的是通常提到的特征包括集体主义、和谐、集中控制,专制和家长式的领导,家族企业,期望努力工作的员工,强大的组织网络和业务联系。这些特点在中国和海外的华人中都有体现,这些实践可以追溯到孔子所倡导的价值体系。这些儒家的五种关系,五德,和儒家的工作伦理。这五种关系决定了适当的行为和角色组织成员;这五种美德为社会提供了道德框架强调和谐的重要性;而儒家的工作伦理强调的是重要的勤奋、忠诚、敬业、节俭、热爱学习。五个关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到人际关系。适当的行为是由儒家思想决定的上级、父母、丈夫/妻子、长辈和朋友。孔子非常关心人际关系和社交礼仪。而孔子并没有把他的建议指向商业组织,这些关系在今天的管理中表现出来中国人的习俗。国王和臣民之间的忠诚孔子提出了以地位为基础的强有力的社会等级制度。层次结构将由一位仁慈的领导人来维持,而他的行动是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科目。这种国王与臣民的关系带有封建色彩;然而,现代的关系已经从对统治者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一个人的组织。等级和等级制度是中国组织的重要方面。在一个典型的中国组织中,决策是由高层领导做出的组织和每个人都应该毫无疑问地执行指示。员工被期望对他们的组织忠诚和奉献,作为回报组织被期望照顾他们。对员工的全面关怀以西方组织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许多中国人的雇员公司会经历一个更家长式的组织,一个可能提供住房的组织,娱乐、教育、儿童保育和其他福利在西方并不常见。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孔子觉得父子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的父亲应该引导儿子,儿子应该尊重和服从父亲建议。就像一个父亲给他的儿子——中国人——提供建议、教导和指导一样经理应该对员工做同样的事情。在儒家社会中,管理者与员工的互动就像一个父亲会寻找最好的他孩子的兴趣。在现代中国的组织中,这种关系得到了扩展现在大部分都包括了男女。孔子觉得这是一种关爱和哺育组织促进了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和谐。中国经理的行为为员工提供良师益友和积极的榜样是实现这一“父子”关系的关键。孔子的关系。夫妻之间的责任这一儒家原则规定了丈夫和妻子应扮演的适当角色他们的妻子。孔子规定了女性的顺从角色。他觉得女人应该这样被限制在家里,不能做决定。女性应该被引导他们的丈夫,给他们完全的忠诚和奉献。妇女不允许这样做在中国的官僚机构中担任重要职位。古代妇女的角色中国是一个内向型的、顺从的国家,即使在今天,这种不平等仍然存在性别。虽然在共产主义下实现了更大的平等,但中国文化依然如此更加强调和重视男性。知觉差异仍然存在中国关于女性在管理中的作用的研究(Bowen, Wu, Hwang,和Scherer)2007)。然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一儒家原则也可以被采纳解释组织中有名无实的领导的适当角色。当组织被视为家庭的延伸,我们发现,领导者的首要角色是行动作为父母的形象,在家庭中保持和谐、尊重和凝聚力组织。所有的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和具体的作用发挥组织。社会控制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宗族倾向和关系是基于预先确定的角色和适当的行为而建立的从这些角色中流出。服从长老孔子主张年轻人应该尊敬长辈。年龄尊重仍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年龄也很重要决定这些组织的向上流动性。这对于年轻的管理者来说并不常见要把握为了超越更多的高级经理,即使年轻的经理更有资格,而按西方标准,更适合提拔。年轻的经理们期望倾听,服从,尊重他们的长者,等待他们的晋升。作为对长者毫无疑问的尊重的交换,这个组织和它的长者希望成员们能照顾到年轻雇员的需要。高级管理人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40364],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