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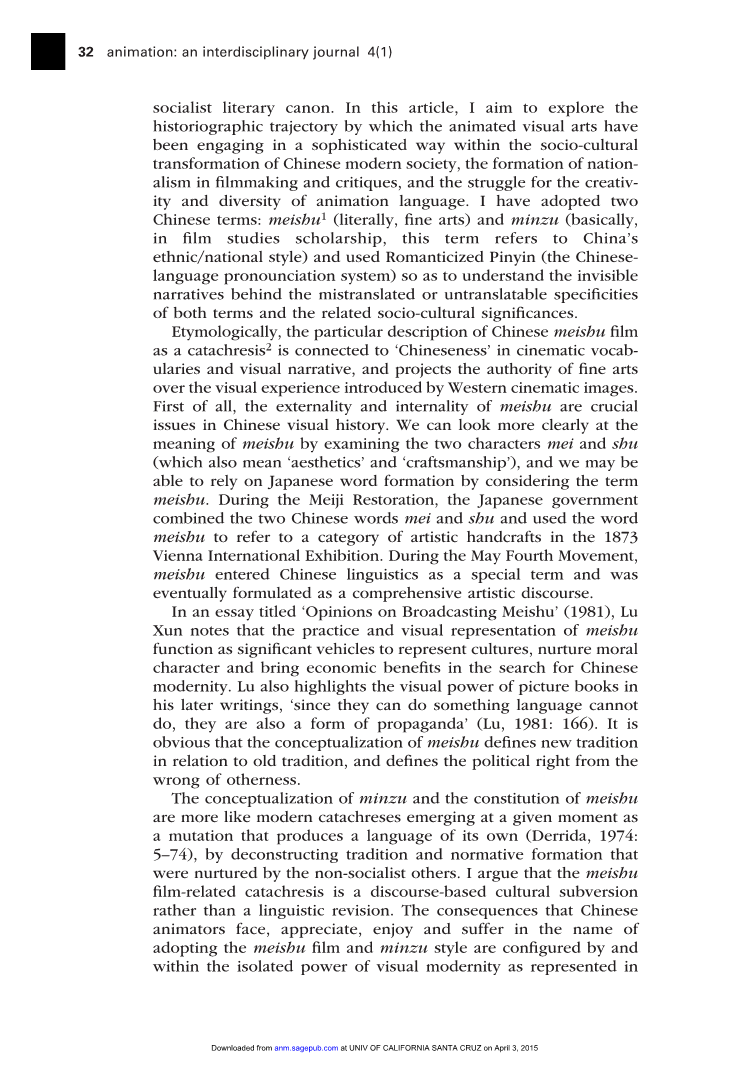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24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纪念美术电影:词语误用与中国动画理论中的隐喻
摘要
本文从历史的悲剧和文化的角度出发美术创作与理论化中的隐喻与社会主义艺术话语有关的电影民族风格。通过调查这些问题,作者从中国学派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美术电影的概念化和构成,并以此作为产生民族主义认同的有力隐喻。这种认同将视觉艺术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带入一个共享的空间,在动画电影创作中再现中国美学。作者认为,美术电影是中国视觉史上一种独特的、民族化的电影形式,它是对民族风格的概念化和中介化,是一种以话语为基础的美学流派,有助于美术电影在社会主义文化和政治中的生存。
关键词:词语误用,中国动画美学 ,中国动画学院,意识形态,美术电影,民族风格,现代性、民族主义
正文
从大多数视觉艺术标准来看,中国动画自1949年以来已成为一种成熟的国家级电影类型,代表着中国现代艺术史与社会主义文学经典之间的电影联系。本文旨在探讨动画视觉艺术在中国现代社会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轨迹,在电影创作和评论中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为动画语言的创造性和多样性而进行的斗争。我用了两个中文术语:美术[1](字面意思是美术)和民族(基本上,在电影研究领域,这个词指的是中国的民族风格 )并使用了浪漫化的拼音(汉语发音系统),从而了解这两个术语的误译或不可译的特殊性背后的隐形叙事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意义。
从词源学上讲,美术电影作为一种词语误用[2]的特殊描写,与电影词汇和视觉叙事中的“中国性”有关,体现了美术对西方电影形象所带来的视觉体验的权威。首先,美术的外在性和内在性是中国视觉史上的重要问题。通过对“美”和“术”这两个字的考察,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美”的含义,通过对“美”这个词的考察,我们也许可以依赖日语构词法。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在1873年的维也纳国际展览会上,将“美”和“舒”两个中文单词结合起来,用“美舒”一词来指代一类手工艺品。“五四”时期,“美术”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进入中国语言学界,并最终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话语。
鲁迅在1981年发表的《关于播送美书的若干意见》一文中指出,美书的实践和视觉表现,在寻求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具有代表文化、陶冶道德品质、带来经济效益的重要载体作用。鲁迅在后来的作品中也强调了绘本的视觉力量,“因为它们能做语言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它们也是一种宣传形式”(鲁迅,1981:166)。显然,美术的概念界定了新传统与旧传统的关系,从他者的错误界定了政治权利。
民族的概念化和美术的构成法更像是在特定时刻出现的现代灾难,它是一种变异,产生了自己的语言(德里达,1974:5-74),通过解构非社会主义者培育的传统和规范形态。本文认为,美术电影相关的用词错误是一种基于话语的文化颠覆,而不是一种语言修正。中国动画人以美术电影和民族风格的名义所面对、欣赏、享受和承受的后果,是由中国动画史上所代表的视觉现代性的孤立力量所构成的。这样的词语误用也标志着一个由汉字诠释的理论框架与西方流行的动画理论模式之间难以沟通,显示出其历史的时间性和不稳定性,从而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动画理论中自我矛盾的民族志的方法:
现代的词语误用虽然意识形态是思想上的且有根据的因此不完全可译.....同时又是大规模的普遍术语。它们既可以在在异性游戏中的两性关系中被解读,也可以作为价值编码或规范意识形态的实体被解读。(Barlow,,2004:32)
Barlow认为,词语误用通过操纵语言意义来追求所谓的现代价值。这个民族国家及其权威的论述在政治上是公认的,它存在于当前和过去地方/全球进程的显著核心。美术、美术电影、民族风格等新词的出现,标志着权力新秩序形成的历史时刻,使跨文化的本土阐释变得不可译。从目前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卡通”一词在汉语中消失了几十年后,作为一种经济的符号重新出现在公共领域。“动画影像”原本是“动画”的唯一翻译,现在已经成为所有与动画相关的作品的常识性描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英文名为Shanghai Animation Studio(SAS)[3]。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动画电影及其相关研究的回顾,这些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话语纠缠在一起,探讨了民族主义与动画美学结合的可能性。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民族风格的兴起和概念化,在中国称之为电影研究的民族风格。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种概念化与中国动画人在处理国家话语和丰富视觉特征方面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审美逃避、妥协和创作实践有关。第三部分提出了美术电影在民族主义、民族风格、追求中国化的文化议程等方面存在的文化隐喻和异化问题。特别是通过这些问题,我想展示美术电影作为中国视觉史上一种独特的、民族化的电影形式,是如何对民族/民族风格进行概念化和对分歧进行调解,是如何形成一种以话语为基础的美学流派,从而在社会主义文化和政治中生存的。是如何建立以话语为基础的美学流派,在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中生存的。
中国动画及其不满情绪的视觉历史
这一部分的标题是“中国动画及其不满情绪的视觉历史”,是对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情绪(1989[1929])的模仿,这是弗洛伊德在阐述他对个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的观点时创造的一个短语,在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和社会对服从的要求之间的支点。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中国动画的新生实践和五四运动的经验,当时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受到爱国主义情绪的鼓舞,渴望用科学和民主的眼光重新评价传统,建设一个新的国家(Chow,1960)。这一时期的历史意义是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在随后的发展时期和社会动荡时期,一种横扫动画实践和研究的专制支配权的释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动画史随后出现的扭曲和简化,谁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张爱玲(又名Eileen Chang)的《关于卡通的未来》(1993)是我国最早涉及动画研究的评论之一。张艺谋认为,动画电影属于卡通形象的范畴,但它应该被视为中国电影的一种主要代表形式,而不是仅仅起到儿童娱乐的作用,这在传统上只是作为故事片的补充而被贬低了。张艺谋对动画观赏性的中心观察与动画在电影表现中所能创造的社会文本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动画片观众需要转变观念和期待,以实现把动画片作为一种独立的视觉艺术形式或新的视觉艺术体裁来看待的价值。A. Zhang (1993)指出,在观众厌倦了传统的迪斯尼米老鼠之后,中国动画将面临一个辉煌的未来:中国动画可以通过激发人类的思想来表达社会生活,以调解知识爆炸和娱乐欲望之间的关系(pp. 259–61)。这一普遍的观点与动画现象学的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有关,这意味着对动画奇观中“中国内容”的追求。由于民族主义是当时电影创作的关键词,电影的中国内容很快就被引向了对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呼唤。接下来是上世纪30年代万氏兄弟的爱国动画《公民速醒!》(1931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精诚团结》1932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狗侦探》(1933年明星影业公司)、《血钱》、《民族痛史》、《航空救国》(1934年全明星影业公司)等。万氏兄弟的每一部动画片的上映都备受期待并广为宣传,因为它们都涉及民族主义情绪。万籁鸣回忆说,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片《铁扇公主》(万籁鸣,上海联华电影公司,1941年)的拍摄动机是“通过强调反抗的必要性来唤起公众的民族精神”(Quiquemelle,1991:179)正如玛丽·克莱尔·奎克梅勒(Marie Claire Quiquemelle)所指出的,这段历史不仅描绘了五四时期万氏兄弟个人奋斗的故事,而且也描绘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独特的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pp. 175–86)。在许多方面,围绕这些动画文本的爱国主义涉及到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民族主义电影通过成为他们的集体标志来制定目标,同时模糊了这些早期动画作品中的权威性、革命性话语和个人、实验性和艺术性努力之间的界限。这种关系与国家生存原则(而非动画片的文化生存原则)密切相关,影响深远,甚至在半个世纪后,在万籁鸣1980年代中期的自传《孙悟空与我》(1986)中,他天真地把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归咎于香港的侨民和他在那里的创造性冲突。意识形态意识明显地与集体爱国主义意识相结合,而集体爱国主义从根本上被约定俗成地成为制作动画的主要标准之一。大多数动画师都被这一传统所束缚,同时也遵循着它的说教和民族化的意图(Wan and Wan,1986)。
在英语学术界,对中国动画的研究大多是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视角展开的,部分原因是本土的复杂性和社会文化的潜台词太模糊,并不清晰可见。吉安娜尔贝托·本达齐(1994)的《卡通片:电影动画的一百年》提供了早期发展的一些基本信息;玛丽·克莱尔·奎克梅勒(Marie Claire Quiquemelle)的《万氏兄弟和中国动画电影的六十年》(1991)阐述了1949年以前万氏兄弟的生活和作品的描述性叙述;布鲁诺·埃德拉(Bruno Edera)的《电影动画的一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画电影》(1980)对中国共产党国有动画作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性格作了概括性的观察;杰伊·莱达的《电影:中国电影与电影观众记述》(1972)是一部自传体文本,只有少数几部介绍中国动画史及其复杂语境的段落。这种文学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国家话语的进步权威和主体性和个体创造性的逐渐消失。相反,它倾向于在艺术史的框架内对中国动画进行分析,试图通过分析了解国有的、非商业的生产体系和审美特征。
Mary Ann Farquhar在《僧侣与猴子:中国动画的民族风格研究》(1993)一书中对民族的描述认为,关于中国动画的辩论有一个超越审美考虑的政治议程(1993:4-27)。她通过对两部动画文本的民族特色和革命内容的取样,刻画了中国动画在中共话语中的特征:《大闹天宫》(万籁鸣,SAS,1961,1964)和《三个和尚》 (A Da, SAS, 1980)。前者标志着中国动画史上中国性的兴起和成熟,后者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性的重生和延续。 然而, Farquhar认为,这种“中国性”作为一种文化标识,可以在民族主义电影制作领域理解,但作为一种源自中国传统艺术的视觉表现(即,作为现代电影语言的对应物:最近对动画中强调的“中国性”的拒绝,是一种回过头来考虑形式和电影语言的评论(p. 23)。围绕着中国动画学派的政治,将在后面讨论,否则将导致过时的思想,这种思想支配着一种理论方法,将中国动画视为一种全国性的思想实践,而不是一种表达传统文化内容之间的斗争的艺术表现语言与视觉现代性。
大卫·埃利希(David Ehrlich)和金田一(Tianyi Jin)的年鉴《中国动画》(2001年)提供了一幅全景图,其特点是长期努力培育“通过多年的内部压抑和动荡形成的艺术形式”(p. 27)。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国有电影制片厂对动画制作的垄断。通过强调在国家话语和官僚主义旗帜下出现的个人创造力,Ehrlich和Jin将最重要的动画师和他们的杰作介绍给国际英语观众。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他们认为,中国动画面临的更大危机涉及在世界市场外部动荡中的创作自由(pp. 7–32)。国家与观众、本土市场与全球资本的争夺,是1949年以来中国动画陷入的困境。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对外开放,这场斗争一直是政治性的、一维的,由此带来了不得不与市场和国家妥协的双重复杂性。尽管正如Ehrlich和 Jin所暗示的那样,政治限制和个性的隐形仍然是困扰中国动画史研究的障碍,但它们却给中国动画文学带来了可喜的成就。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动画创作,通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验的描绘,将党的国家社会主义机器与五四文化遗产架起了桥梁,但其在当时的传播和艺术反思还不成熟,也没有受到国家政策的系统控制。1962年召开了首届中国动画前期工作会议,讨论了动画创作的艺术特点,并试图总结创作经验(张松林,1984:12)。除了关于动画、中国古典绘画和民间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的辩论之外,这次会议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官方将中国动画定义为一种“教育”儿童的说教范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动画研究发表了三部重要的记录片:中国电影年鉴(中国电影人学会)中与动画研究有关的收藏,每年出版一次,包括历史和理论著作;万籁鸣回忆录《孙悟空与我》和《眉湖电影创意研究座谈会论文集》(文化部电影局电影通讯编辑部、中国电影出版社国产电影编辑部,1984)。尽管这些研究倾向于将中国动画置于传统文学和美术领域,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重大的历史问题,并提供了更多的个人叙述,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丢失的那种视角。
最近,对中国动画电影“黄金时代”的中文历史重新解读激增,在这些出版物中被确定为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国有电影。例如,读动画片:《中国动画八十年》(徐和王,2005)、《中国动画电影史》(阎和硕,2005)和《二十世纪动画电影艺术史》(张浩,2002)都是或多或少同质化的一维文化记忆的类似表达中国动画中纯真纯真的中国文化精髓。这些作品强调中国学派的文化认同,既忽略了集体政治权力与审美创造力之间的摩擦,也忽略了对文化垄断的理论思考。许多过去和当代的中国动画文学所表达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妥协,因为它们把中国动画作为一种工具,揭示了国家话语的无懈可击的权威与动画形象的表现之间的基本互动关系,而动画形象的表现大多源自中国传统艺术而不是现代电影语言。这种视角将理论表达视为一种“不满”,并在策略上与民族现代性的追求相配合,构建了五四以来强调“更多中国化”的视觉风格。
中国动画研究很少考虑中国人陈词滥调中自身政治位置的缺失,至今仍处于学术上的模糊状态;似乎很少有人对它的艺术和文化细节感兴趣。在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历史回顾和编年史中,动画的位置只是一片空白,或者被曲解或支离破碎。例如,在尹鸿、凌燕的《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2000)中,动画电影被完全忽略为中国电影的一个范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动画电影制作作为复兴文化产业的核心实践,如今正被重新强调。文化实践的碎片化与中国动画市场的高期望之间的脱节,仍然是中国电影研究乃至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思考之外的问题。
民族风格之路:中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37351],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