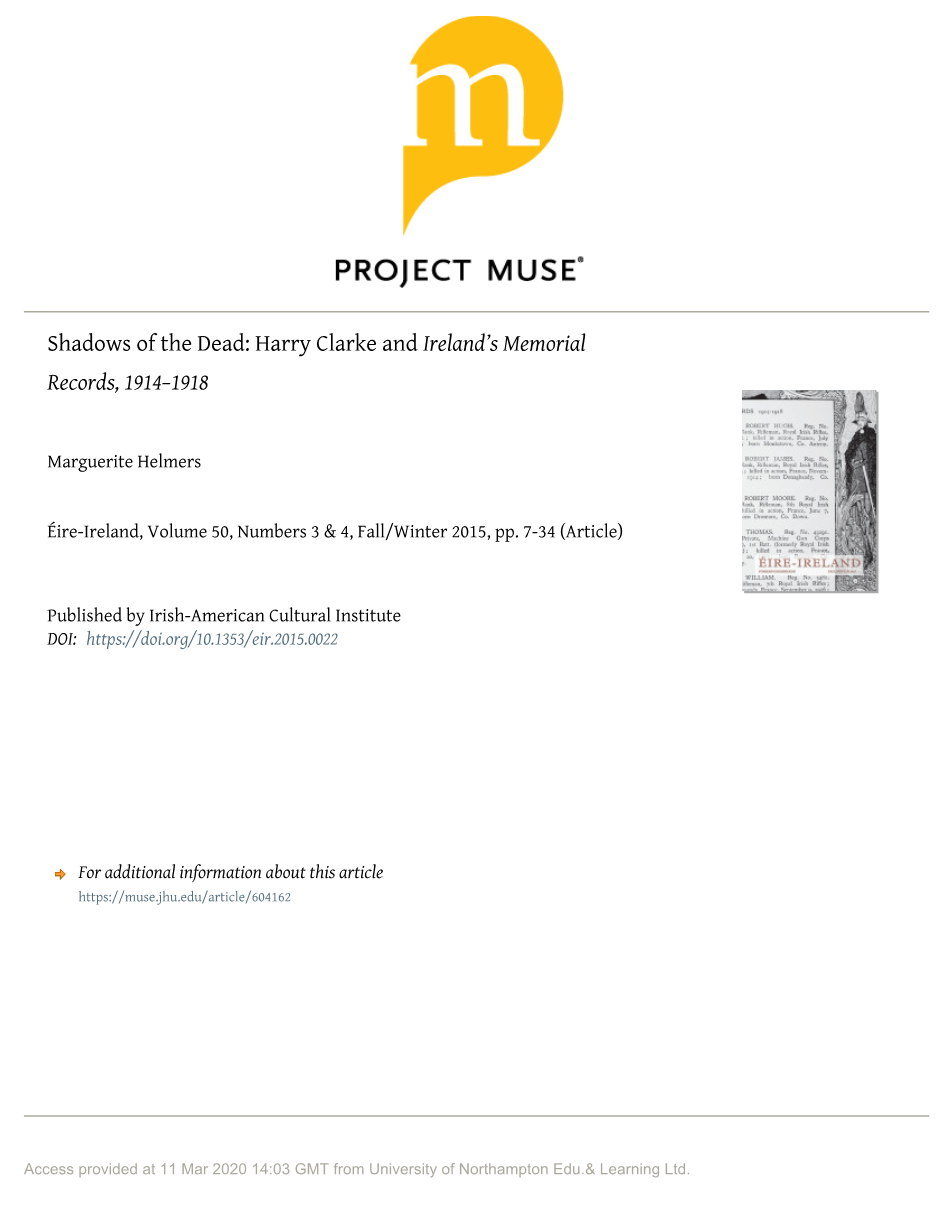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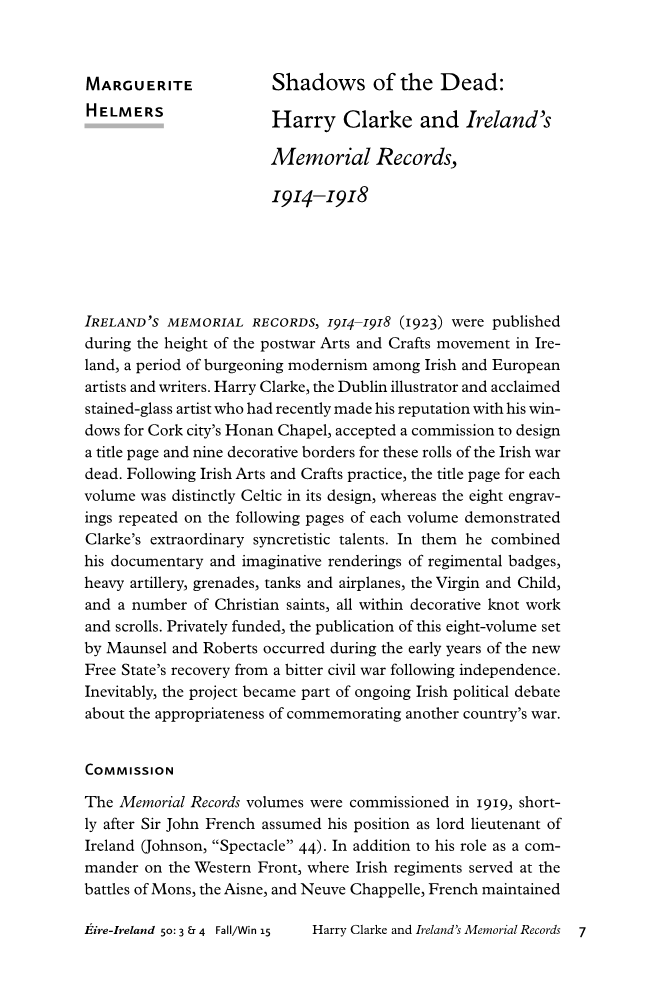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29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亡者的影子:哈里·克拉克与《爱尔兰纪念档案》(1914-1918)
1914年-1918年(或1923年)为爱尔兰战后工艺美术运动的鼎盛时期,也是欧洲和爱尔兰艺术家、作家现代主义萌芽时期。都柏林插画家、著名的彩色玻璃艺术家哈里·克拉克(Harry Clarke)由于最近负责设计布置科克市的霍南教堂(Honan Chapel)彩色花窗而名声大噪。他接受了这个为纪念爱尔兰地区战争死难者而设计的卷轴委托(其中包括一个扉页和九个装饰边框)。随着爱尔兰工艺美术运动的进行,此书每一卷的扉页在设计上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凯尔特风格,而且每卷所重复的八幅版画都显示了克拉克非凡的融合天赋。在这些作品中,他将自己的纪实和想象力融合在一起,将军团徽章、重型火炮、手榴弹、坦克和飞机、童贞少女和儿童,以及许多基督教圣徒的形象,全都融入到装饰性的纽结和卷轴中。在爱尔兰人民结束激烈内战取得新自由之州的独立之后的复苏初期,蒙塞尔和罗伯茨私人资助出版了这八卷书。不可避免地是,这个项目成为了爱尔兰正在进行的关于“纪念另一个国家的战争是否合适”的政治辩论的一部分。
委托
约翰·弗伦奇爵士自1919年就任爱尔兰总督后不久,便委托制作了这些纪念册。除了在西线担任指挥官(爱尔兰军团曾在蒙斯、埃斯纳和新夏佩尔战役中服役)之外,弗伦奇还与尼维尔·麦克雷迪(Nevil Macready)保持着长期的联系。麦克雷迪是第一批认识到“记录西线阵亡军人的埋葬地点”是一项艰巨任务的陆军指挥官之一。停战后,麦克雷迪成为新帝国战争坟墓委员会(IWGC)的顾问。1919年7月18日,在都柏林举行爱尔兰和平日庆祝活动之前不久,弗伦奇在凤凰公园的代理公馆主持了一次筹划会议。在那里,他提议为爱尔兰建立一个国家战争纪念馆——一个理想的、永久性的建筑,里面存放着纪念书籍,那里将成为死者和失踪者家属沉思的场所。
许多民族主义的主要领导人和公民都反对举行庆祝胜利和纪念爱尔兰第一次世界大战死者的仪式。在对纪念活动的矛盾反应中,一些事例可以反映出民族主义者对庆祝活动的反对(或缺席),这便是战后爱尔兰如何看待任何纪念活动的先兆。例如1919年和平日庆祝活动中爆发的“混乱”:当时一群学生唱着革命的“士兵之歌”,作为《上帝保佑国王》的结尾。那些民族主义者不仅记得1919年英国宣布lsquo;爱尔兰自行宣布的“第一监狱”为非法rsquo;,而且还记得爱尔兰早期的死刑、监禁和复活节起义后的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还能生动回忆的事件中,许多都是由担任英国本土部队指挥官的法国人下令进行的报复行为。
直到1938年,在对lsquo;第一次世界大战rsquo;的适宜性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异议之后,英国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Edwin Lutyens)才完成了爱尔兰国家战争纪念碑建设四座书屋的设计。作为IWGC的三位主要建筑师之一,1914年之前鲁琴斯就把几座兰贝岛和豪斯的爱尔兰风格私人住宅翻修成了带有工艺美术特征的大房子,这使得他对战争纪念工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些书室是作为一个在纪念公园里提供展示纪念档案的美丽、沉思空间而存在的。然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座精心设计的公园一直闲置在岛上桥的旧址上,在那里,它遭到了破坏,到处都是流浪者,直到1988年才正式落成。一套完整的纪念档案目前就陈列在公园东南面上锁的书室里。
即便是选择出版纪念档案的出版商也很复杂,这可能反映了忠诚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一致性:前者致力于使用具有极强审美资质的打印厂,而后者则被一家在政治上有大量可靠出版物储备的公司所吸引。一方面,蒙塞尔和罗伯茨受委托完成了这些纪念档案的印刷和装订工作,并因其工艺美术传统中精雕细琢的书籍而获得认可。另一方面,该公司也以出版民族主义文学而闻名。1919年,蒙塞尔的目录包括特伦斯bull;麦克斯韦尼的《革命家》(1914年)、詹姆斯bull;康诺利的《爱尔兰的劳工》(1917年)、爱丽丝bull;斯托普福德bull;格林的《我们在阿尔斯特》(1918年)和德斯蒙德bull;瑞恩的《被称为皮尔斯的人》(1919年)——这些作品与战后的纪念活动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1919年,上尉、诗人、战争老兵——斯蒂芬·格温,和Maunsel and Company出版社的三位创始人之一,2人出席了在总督官邸举行的会议,这可能有利于出版公司。此外,克拉克很可能是在他的赞助人劳伦斯·沃尔德伦的支持下得到这份合同的,沃尔德伦是一位美术收藏家,也是前国会议员。历史记录并没有透露艺术家本人对委员会的看法。他的笔记本上只有“爱尔兰国家纪念碑”几个字和1919年9月29日的日期。
这些纪念档案是在战后涉及所有参战国的大规模纪念运动中产生的。伦敦白厅的鲁琴斯纪念碑于1919年揭幕,现在是英国主要的国家战争纪念碑。 1919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战争纪念馆展览中展出的物品中有威廉·莫里斯的凯姆斯科特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收藏馆的彩绘手稿与莫里斯的作品搭配在一起,“展示了在制作一个美丽的页面时,不仅取决于装饰,而且取决于间距和布局”的道理。凯姆斯科特的原则之一是,整本书都很重要,装订的精美程度不应低于文字和插图。“理想的书”应该是那种“纸张、风格、字体、印刷和插图都”和谐地“体现单一的审美眼光”的书。
1920年,IWGC聘请 道格拉斯·科克雷尔(Douglas Cockerell)作为艺术和技术顾问,为欧洲和中东地区数以千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墓地设计和制作墓地登记表。作为W. H. Smith装订店的经理和托马斯·詹姆斯·科布登-桑德森(艺术装订的领导者之一)的学生,科克雷尔为墓地登记册注入了艺术和手工印刷的细节,同时也在其中建立了统一的设计体系。遵循威廉·莫里斯的原则,科克雷尔认为“登记簿不应仅仅是名单hellip;hellip;每一登记册应包括墓地的正面图、该地区的地图、打造坟墓的施工步骤以及墓地及其环境的说明”。理想情况下,这些内容一旦被安放在每个墓地内一个特别设计的青铜盒子里,IWGC登记册就会被处理和咨询,人们会对其平面设计和印刷的精心设计表示赞赏。毫无疑问,受科克雷尔原则的影响,这些纪念档案体现了一种类似的精神,即把讲故事、设计和纪念联系起来。但是克拉克拒绝了三者相统一的思想,他把他的艺术视野和打破传统的风格注入了《死亡之名册》。因此,他的插图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虔诚——人们大多是被书中恐怖元素所打动。
在IWGC墓地登记和《爱尔兰纪念档案》完成之前,伦敦的英非出版公司已经出版了《牺牲的契约:所有在一战中阵亡的英国军官的传记记录》(1916)的第一卷,书名由拉迪亚德·吉卜林建议。这一纪念档案因其雄心勃勃的开端和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赞助而引人注目。它的编辑L·A·克拉特巴克上校和W·T·杜纳上校打算每六个月出版一册。因此,第一卷列出了1914年8月至12月的死者名单,第二卷则涵盖了1915年1月至6月的死者名单。在这些卷宗中,只有在证实了一名军官的死亡后,才会出现他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条目包括一张官方照片和两到三段关于他的出生地、教育和服役经历的文字。弗兰奇为《牺牲的契约》第一卷写了序言,他评论说,“书中充满了为国王和国家的事业所做的英勇行为和无私的自我牺牲。”他后来还在《爱尔兰纪念档案》的前言中提到了英勇和牺牲精神,并反问道:“在这一光荣的倒下的英雄名册中,还有什么荣誉可以与之相比呢?”
大量的战争死难者似乎淹没了纪念统计项目的编辑们。正如评论家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在研究这些数字意义上的“名字”问题时所反映的那样:“人类的想象力被迫尽可能具体地看到了100万死者的样子”。此外,收集所有的名字是一项艰苦而又耗费感情的工作。《牺牲的契约》的前言指出,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死亡人数是“史无前例的巨大”,而且“军官与士兵的比例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场战争”。《牺牲的契约》在前两版之后就停止出版了。同样,《爱尔兰纪念档案》的编辑们遗憾地指出,他们未能完全完成任务,因为他们无法列出“在海军、空军和殖民地兵团中阵亡的爱尔兰人的姓名”。官方频道显然无法完成列出所有战争死难者名单的任务。
尽管如此,这种牺牲精神为出版纪念册开创了先河。乔纳森·万斯指出,“服役名单[荣誉名单]的公布在停战后的几年内达到高峰,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以健康的速度持续”。由于从未找到这么多的尸体,也由于已确定没有任何来自大不列颠或英联邦的尸体会被遣返,因此出现了对纪念牌、方尖碑和记录的明显的公共需求。杰伊·温特(Jay Winter)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战争初期的情况上,他描述了负责埋葬任务的士兵们“简单地把尸体丢进集体坟墓,而没有取回身份标签”。因此,成千上万的家庭通过电报得知他们的家人失踪了,估计已经死亡。这种看似残忍和轻蔑的方式来记录这些人的服役记录,便是警醒人类应该具有一种更合乎人类生活道德和更敏感的认知,一种能说出死者姓名并认可其家庭牺牲的认知。谈到在加拿大纪念仪式中给死者起名的重要性,万斯得出结论说,收集这样的荣誉名册和纪念册是“国家试图建立战争记忆的核心”:
与当时的其他纪念档案相比,爱尔兰的纪念档案具有不同寻常的包容性,因为它们不仅包含了爱尔兰全部32个郡的死者姓名,还在不考虑他们的出生地的基础上列出了那些在战争中为爱尔兰军团服役的人的名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尔兰军队卷入了所有的战争,有三个特别的爱尔兰师——第10师(爱尔兰)、第16师(爱尔兰)和第36师(阿尔斯特)——1914年作为基奇纳勋爵的新军队计划的一部分而建立。虽然爱尔兰人在所有的英国军团中服役,但这三个特别的爱尔兰师成为了招募新兵的工具和骄傲的源泉。
英雄主义和救赎
克拉克为《爱尔兰纪念档案》所作的细密镶边强调了崇敬和讽刺之间的微妙的相互作用,这是他的才能的特征,这在他为埃德加·爱伦·坡的《神秘和想象故事》(1919年)所作的插图中便体现很明显了。因为克拉克在这非凡的荣誉榜上绘制的是插图,而不是纪实的照片,正如劳伦斯·普雷利(Laurence Prelli)指出,“把lsquo;更多可能lsquo;的意味提供给遇到他们的人”是最好的手段。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士兵的剪影,他们似乎在书页上翩翩起舞,背后是弧光灯,脚边是漩涡状的海水泡沫、薄雾和树叶。例如,他们提出了凯瑟琳·泰南1914年的诗《加入颜色》中的诗句: “他们唱着歌从雾中走出来/走进雾中”(图2)。如前所述,在扉页之后,有八幅版画围绕着姓名、军衔、兵团、死亡日期和死亡地点。克拉克的插图可以按主题进行分组和研究:在设计中带有凯尔特人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在扉页;传统的基督教意象,它有助于形象的叙述和可能意义的范围;以及战争题材的插图,克拉克经常在书中描绘战争场面。
图2.“他们从雾中走出来/走进雾中,唱着他们经过的歌。”哈里·克拉克。《爱尔兰纪念档案》1914-1918年
严格的扉页设计最能体现凯尔特风格, 以苗条的希伯尼亚(或艾琳)形象为主,爱尔兰作为一个女性的化身(图3)。她手拿火炬,站在猎狼犬旁边,面对着传统的凯尔特十字架和一座圆塔,象征着爱尔兰博学和宗教历史。围绕着希伯尼亚和四个天使的页面的两侧是交错的凯尔特设计模式。克拉克在他的作品《光明福音》和彩色玻璃肖像学之间强调了两者的相似之处。四福音派——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经常被描绘成手持一本书;然而,克拉克在书的扉页上为四翼人物安排了爱尔兰四省的徽章:明斯特、莱因斯特、康奈克特和阿尔斯特。
图3. 扉页
今天,克拉克因其精湛的艺术技艺和独特的视觉风格而备受推崇。最著名的是科克霍南教堂的十一扇窗户。其中,他描绘了九位圣徒,包括圣帕特里克、圣布里吉德、圣哥伦西勒、圣芬巴尔、圣伊塔、圣阿尔伯特、圣戈布奈特、圣布伦丹和圣德克兰,而且还知道另外两个传统的基督教人物,我们的夫人和圣约瑟夫。他不仅知道与当地圣徒有关的装饰图案,而且还知道传统基督教图像和象征手法,这在《爱尔兰纪念档案》中再次得到了证明:在书中,插图中不具有类似士兵的轮廓,圣徒和天使都有非常精致的面孔和衣服,暗示他们是处于永生中物质和肉体的存在。在纪念档案的镶边内有几位天使,除去圣母玛利亚和基督的孩子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对启示录的暗示。当克拉克用装饰的羽毛、玫瑰和藤蔓围绕着圣徒和天使时,他在视觉上加强了对战争影响的诠释,这些藤蔓具有与复活有关的传统象征意义。
除了书的扉页上的四个天使之外,第一页的名字中还出现了一个精致的天使,头上戴着象征胜利的月桂叶(图4)。在这个天使的周围,一个点状的图案暗示着有毒气体会自己分解成玫瑰的形状,这是圣母的象征。在后来的一幅画中,一位同样飘逸、几乎透明的天使手持一个圆形的月桂花冠(图5),他精心制作的翅膀是用鸵鸟羽毛制成的,也许是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时尚的启发。克拉克对服装的兴趣在他的书《插图和彩色玻璃》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中世纪、巴洛克、洛可可和当代的服装风格之间自由流动,他对面料、图案、刺绣和珠饰的细致描绘总是显而易见的,就像纪念档案中圣徒和天使的服装一样。例如,在同时期的作品《彩色玻璃窗》、《十字架与爱尔兰圣徒的崇拜》(1920年)中,克拉克用浪漫化的中世纪束腰外衣覆盖着神圣的人物;这些女人戴着风格化的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钟形女士帽子。
在《爱尔兰纪念档案》中,圣母和圣婴明显地交织在第二页的外边缘(图6)。在它们的对面,在细长的内边缘,克拉克复制了雷金纳德·布洛姆菲尔德(Reginald Blomfield)为IWGC设计的牺牲十字架。圣母玛利亚、圣婴和十字架这两个形象被迷宫般的树叶环绕,从而得到神的理解并与神像相结合。在《爱尔兰纪念档案》中,圣母玛利亚无疑是这个纪念成千上万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爱尔兰母亲所映射的关键人物。
图4. 一个戴着桂冠的
天使,象征着胜利
克拉克还利用他对圣徒属性的广博知识,设计了纪念档案的镶边:在某些情况下将影射战争死者的形象和圣徒的形象相结合。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一个戴着骠骑兵头盔的黑暗而沉思的骑士。第15个轻骑兵的徽章出现在他对面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36886],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