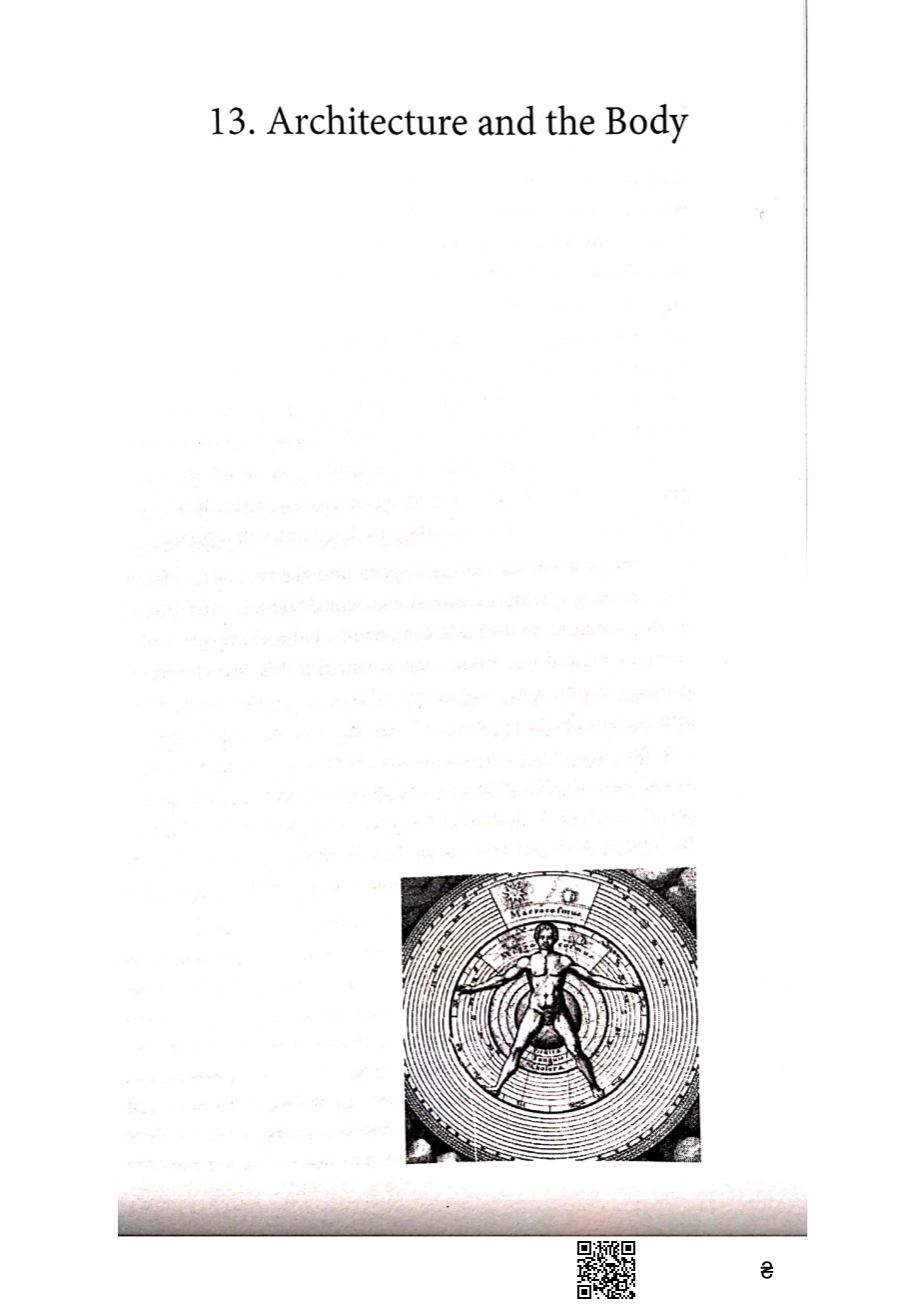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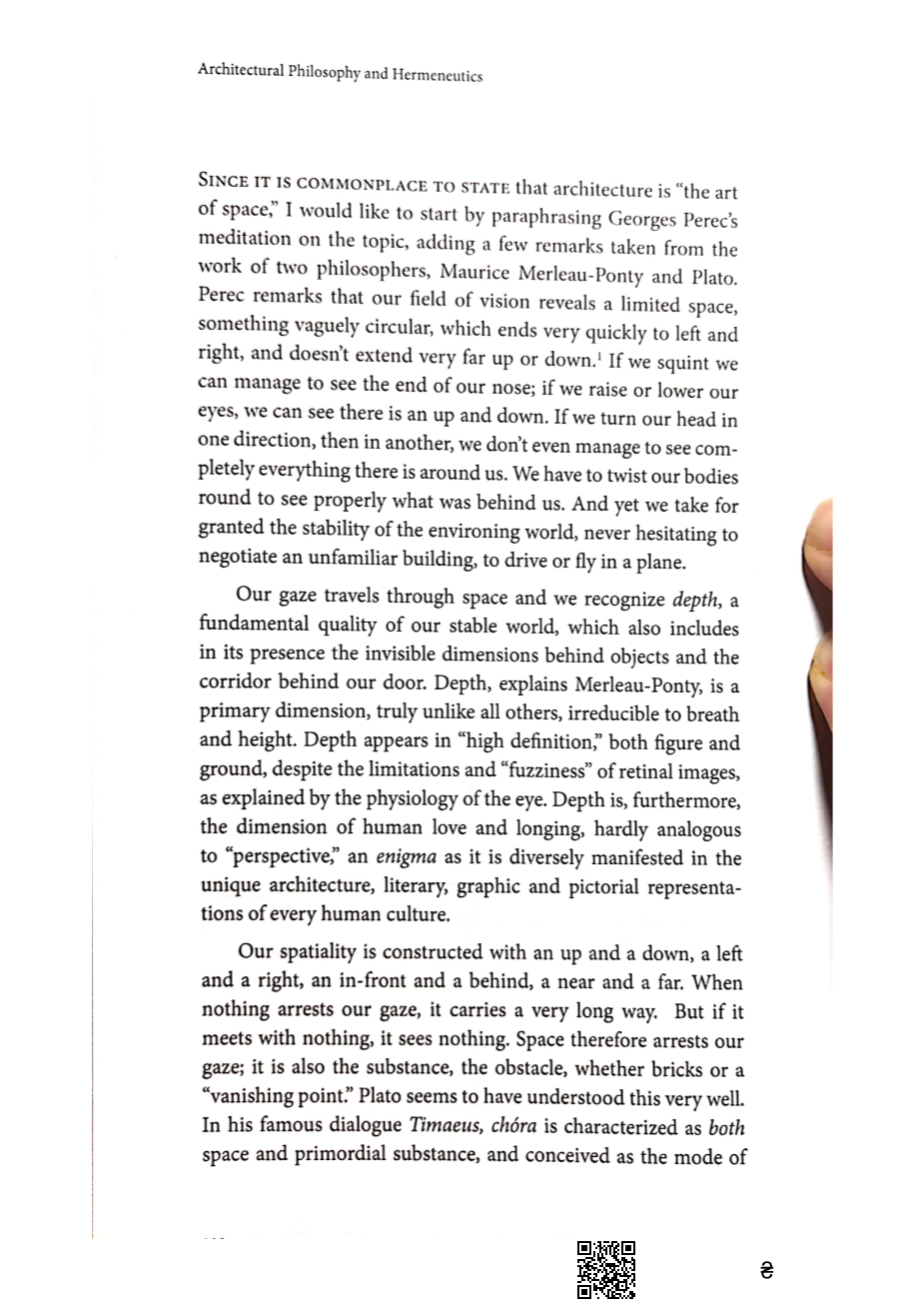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5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建筑哲学与诠释学
如果存在建筑的历史本质,就不能简单地从一组客观化的建筑物,理论或图纸中推论得出。这个词本身是西塞罗(Cicero)时代的拉丁发明,其定义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建筑的现实及其意义是复杂的,随着历史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我也报有相同的想法:类似于人类的状况要求我们解决相同的基本问题,以解决死亡率以及语言所带来的超越的可能性,同时期望针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多样化答案。
建筑拥有自己的“话语世界”,在过去的千年中,它为人类提供的不仅仅是实用主义必要性的技术解决方案;事实上,它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身心健康和自我理解。其根本原因很简单:环境是人类意识的组成部分。根据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汉斯·乔治·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见解,我想指出,建筑开辟了一个交流的空间,提供了将自己视为完整的可能性,以便诗意地居住在地球上,从而是完全的人类。建筑的产品是多种多样的,从古典的古代建筑到维特鲁威斯认为是建筑的主要“部门”的地精,机器和建筑,应有尽有。从巴洛克时期的花园和短暂建筑,到已建成和未建成的“现代性抵抗体系”,例如勒·柯布西耶的《 La Tourette》,高迪的《巴特罗之家》或赫伊杜克的《 Masques》,这种认识不仅是语义上的对等;还是在经历中发生,既是情感上的,又是认知上的,就像一首诗一样,它的“含义”与诗本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情色事件,它泛滥了任何还原性的释义,使观众不知所措。
鉴于这些观察,任何限制我们学科的认识论基础的愿望都主要涉及语言的适当性来调节我们作为建筑师的行为,但它永远不能假装“减少”或“控制”的含义。问题是要确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阐明建筑和城市设计在我们的技术社会中可能发挥的伦理和诗意作用的理论话语。
超过两个世纪以来,建筑理论一直被认为是应用科学的一种形式。无论是技术上的关注还是形式上的关注,建筑师所偏爱的认识论工具都是一种方法论,旨在寻求针对商品生产的更有效的专有技术。这些方法极大地促进了地球的城市化,但它们忽略了道德和文化价值,常常产生疏远的环境。让享乐主义和技术效率驱动的将理论简化为“功能的功能机制”最早是在19世纪初期由让·尼古拉斯·路易斯·杜兰德(Jean-nicolas-louis Durand)书面提出的。早期的建筑理论总是关注更广泛的文化意义问题,与美和真理相关。今天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考虑一种激进的替代方案。延续一种风格或时尚的辩证法是毫无意义的,就像认为建筑只能提供物质上的舒适和庇护一样:这两个概念都来自于杜兰德的著作。此外,仅仅以多元化和多样性为借口来寻求支离破碎和片面的答案是不够的。建筑师的首要责任是能够在此时此刻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在进步知识或破坏性策略的主题下推迟回答。
第一步是弄清楚话语在实践中的作用,这是传统上通过长期的学徒训练获得的。我们的建筑哲学和诠释学数字时代的普遍和错误假设,即保持其含义仅等同于信息交流,甚至使这种讨论成为可能。项目的实现显然需要更多紧迫的不同种类的知识,包括专业信息。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将建筑话语的本质概念化,一种可以导致实现建筑工作所需知识的工作层次的言语表达方式?
继希腊哲学的脚步后,维特鲁威的十本书坚持了mathemata的重要性(稳定的原则,以数学为代表的),对于theoria是指宇宙的规范秩序的理解,尤其明显的比例动作的名人,对于技术而言,可以从大师传授给学生的艺术或手工艺的专有技术。然而,传统理论也承认,意义和恰当性等关键问题需要自然语言,而自然语言本身仍被认为是数学的基础。这类问题不能简化到同样的清晰度,例如算术比例或三段论。还有总是相对于“历史”来理解适当的礼节。例如,某个地点(一个地点)或某种专栏(Doric,Ionic)对于特定程序的适当性取决于建筑师理解作品的能力。例如网站的适当性(一个地方),或一种列(多利安式、离子),一个特定的程序依赖的能力架构师理解手头的工作与先例的通过故事,这在前现代时期也被称为神秘的开始。
我们已经了解到工具性和处方性只是体系结构话语的部分内容,它们都不能说明它们解决的操作的潜在意义或帮助实现。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该词通过其最初的能力讲故事阐明了意义的可能性,因为它以尊重经验空间,即宇宙(传统)或历史(现代)世界和“期望水平”为目的来命名意图。因此建筑师的语言想象力的投射为共同利益构筑了美好的未来。尽管在将建筑作品投放到世界并在公共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时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作品含义和社会价值的最终不可预测性,但是这个词必须为我们表达意义的意图服务。事实上,尽管非工具性语言(诗歌或冥想性语言)与创造之间的运动不可避免地是不透明的,但现象学的赌注在于,一个思考的自我与一个人的行为和行为之间的连续性是可以把握和培养的。为了举止得体,我们必须学会说话得体,这是建筑学教学和实践的一个明显要求。因此,我们在自己的学科中简单地认为理所当然的碎片化和工具性必须受到批判性的审视。
如果通过这些术语我们理解启蒙后理论意义上的排他的、自主的价值观,那么建筑的问题不仅是“美学”或技术问题。建筑实践必须以共同利益的观念为指导,保持政治上的理解,即在可变和凡人的世界中人类寻求稳定和自我理解的政治维度:诱使我们促进正义的一种交流的空间,因此对于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化的理论,不管它们是由技术、政治或形式主义的需要驱动,还是由模仿科学模型的愿望驱动,总是无法解释这个维度。什么样的话语可以被假定为主要的元话语?我认为可以在最近的解释学本体论中找到解决办法,特别是在哲学家的著作中,如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保罗·里克尔和吉阿尼·瓦蒂莫。我提议将建筑理论解释为诠释学,理解为对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晚期哲学中存在的重要本体论见解的语言投射。
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一些额外的历史背景是必要的。与其假设科学思想和建筑理论只是在最近才联系在一起,不如在我们西方传统诞生之初就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他们的目标总是并行的。哲学作为科学是毕奥理论的最高成就,旨在揭示真理。自柏拉图的提马俄斯以来就理解为一个数学对应的真理。柏拉图的《提马乌斯》不仅在牛顿物理学达到顶峰之前成为科学的模型,而且还是建筑理论的模型。Platos demiurge是一位工匠/建筑师,在原始空隙的空间中,从与该空间相当的原始物质(一种通用的塑料物质)(chasho / chaos / chord)中,用几何形状创造了世界。同样,古典时期的建筑师从来不是虚无的创造者;通过模仿技术能力(艺术/工艺)来揭示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建筑通过揭示月球下世界的宇宙秩序来揭示真相,通过类比来显示自然和我们生命体的奇妙秩序。这是一种精确的知识形式,它体现了人类行动,政治和宗教仪式的节奏,从而保证了人类经验的有效性和现实性。有人可能会辩称,建筑理论是科学,与科学具有相同的地位,而与实践却处于非仪器关系。 Scientia提出了应该考虑的东西,即建筑在体验的时空中所体现的比例顺序,不仅体现为建筑物,还体现为人类处境。
正如我在其他著作中试图表明的那样,这种现状在17世纪开始改变,尽管在理论论文中经常明显的变化直到19世纪才影响到建筑实践,这在他的《五种圆柱专论》中颇有争议。 (1683年),克劳德·佩罗(Claude Perrault)质疑了比例在保证微观世界与微环境之间关系方面的传统作用以及光学校正的重要性,而光学校正一直被认为是理论论文与建筑中比例处方之间存在任何差异的原因。在以前的所有建筑学论文中,按比例保持的保证和关于光学校正的论点都证明佩罗已经很好地确立了不能让步于传统的随机实践:根据现场和程序调整比例,建筑为动觉和综合提供和谐体验的能力被一个人感知。对于佩罗而言,理论地位不再是神话或宗教真理的地位。正如新的笛卡儿物理学一样,理论公式只不过是“最可能的、数学上最精确的、由分析观察得来的”。理论论述的目的是尽可能容易地“适用”,一套控制建筑实践的方法。在他看来,建筑实践总是容易出错,而且容易受到笨拙的工艺的影响。佩罗设想建筑及其应用理论是一门参与进步历史的学科,它很可能在未来得到完善。
从某种意义上说,佩罗只是延续了建筑学作为科学的传统。然而,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建筑理论和实践的本质。他的立场结束了一种构想和制造与宇宙学图景相关的建筑的方式,成为了有意义的人类行动的最终的、主体间的框架。我们建筑危机的开始并没有追溯到几年前的先锋派的结束,甚至没有追溯到泛光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开始,也没有追溯到20世纪早期美术的消亡。相反,它必须与现代科学的开端及其对建筑话语的影响相提并论。在佩罗之后,特别是在杜兰德(Durand)之后,建筑理论和实践的合法性通过与现代科学认识论的结合而自然得到了宣称。因此,建筑理论被简化为纯粹的工具:其价值取决于其此后的适用性。
由于对建筑历史的漠视,强调当代实践的这种普遍误解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建筑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要从多方面考虑的文化秩序,具有重要的认识论联系,这种特性体现在各种文物中。这样的建筑历史不可能简化为建筑物的类型学或社会学,也不能简化为单一的,渐进的或连续的线,也不能简化为不连续的封闭的时刻。此外,历史不必成为实践的负担,因为它是20世纪初由反对美术教育模式的“现代运动”先驱们所构想出来的。尼采在1874年写的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历史对生命的作用和不利之处》中,阐述了历史对一个新人,特别是对后宇宙论时代的有创造力和负责任的个人所带来的危险和可能性。当然,历史是无用的和有问题的形式,特别是伪客观的鼓励为自己的利益而保存旧事物,对旧形式进行纪念性复兴的解释性的阐述,给我们一种我们是“后来者”和站在巨人阴影下的小矮人的感觉,并致使无法采取重大行动。但这不应导致漠视历史。在没有宗教和社会认可的神话的情况下,历史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对我们过去的回顾。尼采得出结论说我们需要历史作为生命的食物,记忆作为创造力和先例的食物,以便在没有绝对道德真理的情况下指导我们的行动。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理解和“使用”历史作为伦理创造的框架。自十九世纪以来,缺乏生活的传统建筑实践,我们实际上是叫它重构。它探寻和解构我们的过去的蛛丝马迹,总是用新的眼光去发现迄今为止隐藏的将来有帮助的可能性,就像恢复一个海底珊瑚,或是从看上去普通的软体动物身上提取珍珠。
最近,从科学到启蒙运动中对批判性理性项目的谨慎尝试的方法论中,关于多种意识形态融合的建筑的许多著作经常重申历史的观点,即历史仅仅是一个或多或少无关紧要的先例的积累。对世界和社会的现代和后现代理解,炫耀了这种当代写作所固有的“优越”积极理由和民主价值观。这种对历史的批判性评价很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与流行的线性时间性和技术进步的假设不约而同,认为过去是一本陌生的、封闭的书。因此,它倾向于将科学理论(混乱),哲学结构(折叠,解构)或意识形态模型(马克思主义)外推到建筑理论中。这些被用来为建筑提出正式的策略,隐喻性的连接本身只是一种现代性的习惯。实际上,除了两个世纪前的杜兰德(Durand)开创的应用科学理论和技术实践之间的关系之外,这些策略似乎没有提供新的可能性。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大约十年前,许多追求这种方法的建筑作家,特别是在北美,宣称这是“理论的终结”。
十八世纪的欧洲人见证了历史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像我们在新闻中听到一个政治人物签署了和平协议一样,都只是“创造了历史”。与普遍的认知相反的是,被认为是人类产生的历史它的变化不是“自然的”,而是现代西方意识的一部分,与现代假设性科学(Galilean)不可分割,后者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实验和技术行动“证明”其假设的真理。培根之后,现代哲学和科学的未来方向导致人们对发展和物质进步的痴迷。可以这样说,在启蒙运动之前,尤其是在詹巴蒂斯塔·维柯和让·雅克·卢梭的作品之前,人类的行为被认为或多或少与明确的创造秩序无关。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将目光投向了过去,但只是为了确认其与宇宙学秩序的和解行动,而宇宙学秩序被视为绝对超越历史的永恒,就像历史无疑是救世主的神圣叙事,因此灾难近在眼前。然而,现代历史始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类行为真的很重要,它们可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有效地改变事物,有可能取得“真正的”进步,也有可能自我毁灭。因此,现在与过去在本质上有所不同。这种“载体”的确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它的绝对霸权受到尼采的首次质疑,最近又受到后现代文化评论家的质疑。
我同意吉安尼·瓦蒂莫斯(Gianni Vattimos)的看法,尽管历史作为进步和前卫的宏大叙事可能已经结束,但我们仍必须接受我们的历史性。我们永远不能简单地克服现代性并将其抛在后面:相反,我们可以治愈怨恨,治愈自己,调和我们的现在与过去。换句话说,是时候拥抱而不是试图解决自世纪以来与我们人类状况相关的难题。我们不能表现得好像生活在一个宇宙学时代,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因为这种永恒的存在可能使建筑形式与其用语言表达的预期意义之间的区别无关紧要,从而导致我们放弃对我们的行为在社会政治现实面前的责任。我们也不能假装继续以其未来的方向,对规划和社会工程的信念以及对形式的荒谬无视而继续进行现代性的计划,而转向实用的功能主义,这隐含地否认了建筑的意义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类来体验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修改我们与历史的关系的条款,接受各种话语和传统,同时承担我们个人的责任,通过我们的想象力来投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即我们一生的真正窗口,谦卑地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这就是解释学的论述旨在达到的目的。很明显,在今天这个复杂的技术系统的世界里,我们能自己控制的东西很少;然而,我们的行动,甚至是决定回收纸张的行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荒谬的情况本身就是我们的技术现实,我们完全构建的世界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建筑中的形式主义策略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不管它们的参考框架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或女权主义理论、语言学、物理学或进化生物学中)。
另一种选择是,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它的历史根源出发,构建一个理论。正如维柯早在18世纪就意识到的那样,除非将新兴语言(诗性和多义性)视为人类解决其与生俱来的,有关人类存在的基础问题的基本手段,否则这话语不能被认为是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54921],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