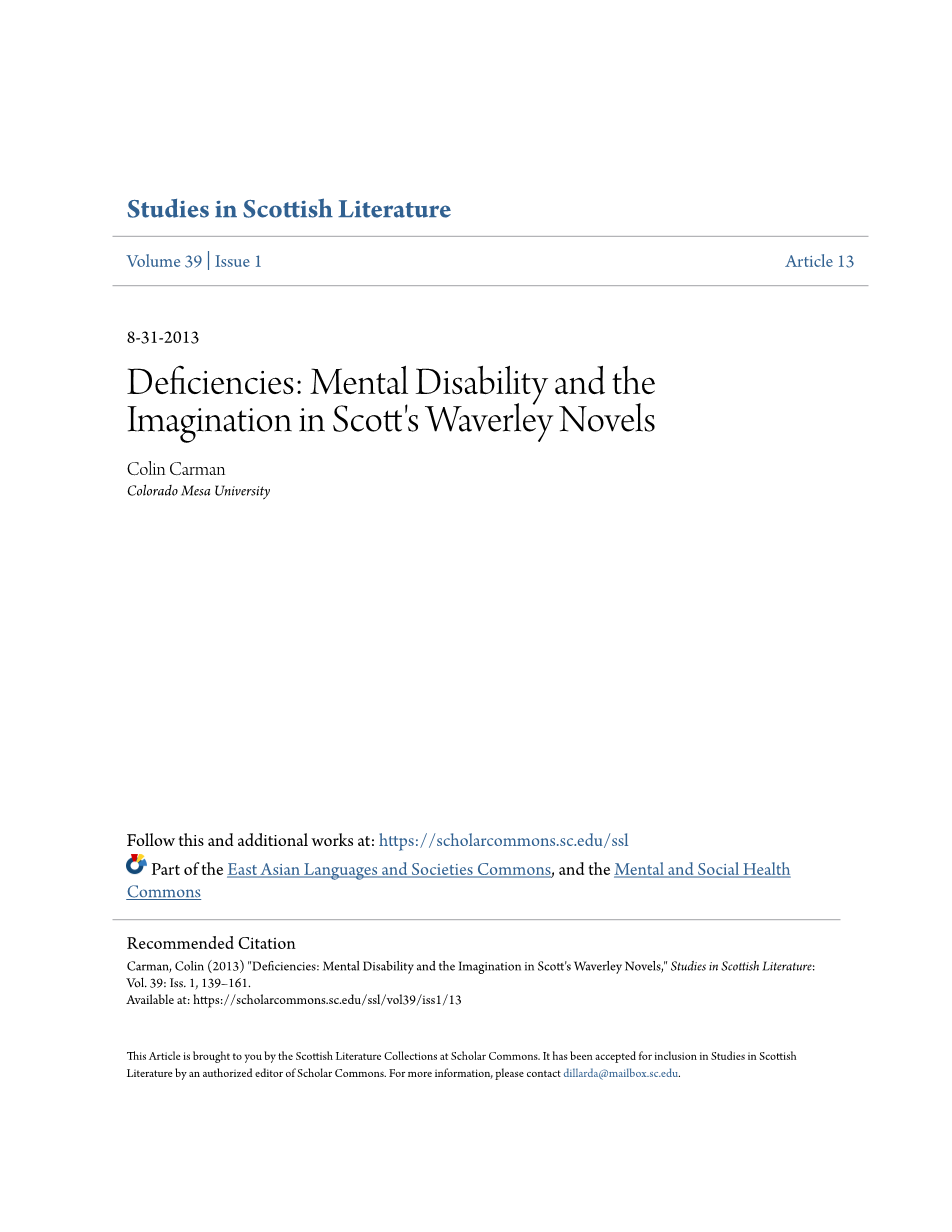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24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缺陷:精神残疾和斯科特·韦弗利小说中的想象力
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韦弗利》(Waverley)和《中洛锡安之心》(The Heart of Midlothian)记录了19世纪苏格兰对精神病患者的态度的转变,并且这两本小说都是以下对精神残疾进行分析的核心,因为在斯科特的历史小说中,它是在傻子和疯子的伪装下运作的。疯狂的社会历史学家很清楚,在1800年代初期,英国对精神疾病的控制和表面上“治愈”的方式进行了全面改革。在1816年至1819年之间,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提出了不少于三项改革法案,其中详细介绍了美国三家慈善医院虐待囚犯的情况,包括贝斯勒姆,约克庇护所和圣路加福音。在伦敦Bethnal Green的两个最大的私人疯人院中,一名患者在潮湿和老鼠出没的牢房内患上坏疽和肺结核后脚被截肢,至少有100名囚犯死于1810年11月冬季出现的斑疹伤寒。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关于精神病患者的福利的公开辩论,并且公众被国王已经精神错乱的传闻所震惊。苏格兰社会见证了精神病医生和其他当局在精神病院外兜售新疗法的爆炸性增长。
爱丁堡皇家内科学院院长安德鲁·邓肯就是其中之一。他谴责说“贫民疯子的悲惨处境,即使在苏格兰这个繁荣,繁荣和慈善的大都市中也是如此。”邓肯(Duncan)在给苏格兰女王陛(1818年)的信中,呼吁迅速建造四个新的疯人院:一个在爱丁堡东区,另一个在格拉斯哥西区,第三个在南邓弗里斯区,还有一个在阿伯丁北部。邓肯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他的民族主义。他认为,爱丁堡必须与伦敦保持同等水平,因为“我们远远落后于英格兰的同胞”,其1808年和1811年的议会法案更好地照顾了精神病患者,这对苏格兰自己的“人道立法机构”构成了严峻挑战(7-9)。邓肯的改革梦想最终将得以实现:到1820年,当邓迪的公共收容所开放之时,蒙特罗斯,格拉斯哥和阿伯丁的其他收容所已经开始运作。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读到了斯科特(Scott)对白痴和疯子的描述,这在19世纪苏格兰对待精神病人的人道主义倾向有着重要贡献。在《韦弗利》(Waverley)中,在《韦弗利》中,一个名叫戴维·杰拉特利的小角色母亲极力保护儿子,但她却认为自己的儿子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傻,并以此来评论儿子低下的社会地位。在将戴维比作华兹华斯1798年抒情歌谣的傻瓜男孩之后,斯科特效仿他的诗意寓意,用珍妮特·盖拉特利(Janet Gellatley)的方言辩护她的智障儿子:“戴维不像其他人那样,普休耕地”,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戴维的故事”(W 321)(320)。她通过讲述这个故事来证明戴维对他的主人布拉德沃丁男爵的忠诚,同时也通过讲故事来引起人们的同情。在《中洛锡安之心》(The Heart of Midlothian)中,斯科特以Madge Wildfire的形式提供了精神残疾(在这种更为暴力和令人不安的例子中,精神错乱)的另一种表示形式,其“完全精神错乱”可归因于母亲谋杀了其私生子。小说中的女主角让妮·迪恩斯(Jeanie Deans)拥有斯科特所说的“对麦奇历史的黑暗洞察力”,这时可怜的疯子狂热地谈论着母亲何时抓捕和屠杀了她的新生婴儿:“我觉得她埋葬了我所有的智慧,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是我自己了”(HM 276)。在这里,斯科特自己对认知障碍的描述也与华兹华斯对“格拉斯米尔的诗人”的典故有关,“他的荆棘诗”预示着婴儿杀手在Madge的精神崩溃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一个人状态不足的原因。 为了使头脑敏锐的珍妮(Jeanie)善于看待这个“狂暴的疯子”,必须通过叙事来解释和维护思想 (HM 273, 271)。
尽管如此,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还是那个时代的人,他的小说反映了许多对弱智人士的偏见。 戴维(Davie)和麦迪(Madge)就值得忧虑。 他们是神秘、混乱的人物,尽管这些负面特征未能影响到他们被同情,因为斯科特笔下的白痴和疯子也拥有强烈的想象力,尽管有限。 斯科特(Scott)的作品表明,精神不健康的人实际上可以进入崇高的精神状态,这是崇高的浪漫主义者珍视的。即富有想象力的大脑,根据科尔里奇所说,“生命力”是“全人类感知的主要动力”。 精神残障人士,无论是“贫穷的简单人”戴维·盖拉特利还是“贫穷的疯子” Madge Wildfire,都同时拥有残疾与能力、精神缺陷的黑暗之谜和理性之光、精神错乱的自由,以及对理性的压抑。(W 317,HM 363)。
在苏格兰精神病学的历史中,斯科特努力将智障人士人性化,有两点似乎特别有用。一是试图使这一时期与智障人士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变得可见,从而将残障纳入未充分代表的、更大且仍在不断出现的历史中,或是在休斯顿于18世纪苏格兰的《疯狂与社会》中所称的“自下的历史”。从术语上讲,“残疾”是一个当代术语,但绝不是过时的。它是一种了解诸如斯科特的不可治愈的白痴和精神错乱之类的状况的合适方法,因为这些这些较差的认知状态被反复定义为与更有能力和想象力的人有关。 简而言之,苏格兰叙事者将愚蠢和精神错乱“禁用”,他将这种生存能力作为自己主权的标志。简而言之,白痴和疯子被这位苏格兰叙述者描绘为“残疾”,他将这种生存的力量作为他主权的象征。
这一论点的一个辅助目标是将斯科特的历史小说中的“残疾”定位为解释性透明性的特殊认识论障碍,因为主观性与历史学作家的整体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斯科特(Scott)看来,白痴和疯子恣肆的头脑必须被说话人控制,因为障碍经常出现,正如米切尔(Mitchell)和斯奈德(Snyder)在《叙事假肢:残疾与话语的依赖性》中指出的那样,“价值主导型行为”凭借残疾及其不确定的病因可被“叙事所破坏”。本文认为,残疾能够使叙事成为可能,因为它似乎促进了叙事的行为,以至于尽管有身世和历史能够解释一个人残疾的起源,但白痴和疯子却促使作者尝试判定和处理这些情况。斯科特(Scott)在《韦弗利》(Waverley)中的代表是富有想象力的爱德华韦弗利本人,他在与戴维(Davie)见面时耐心地听着那个白痴男孩背诵一首民谣。这是对《韦弗利》(Waverley)引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回应,但是那个男孩,让斯科特想起索斯的《毁灭者萨拉巴》里的女巫,“没有传达任何信息”(W 41)。这种可解性的缺乏是使韦弗利的思想和解释行为本身既沮丧又方便的原因。一段时间以来,精神异常的历史学家从福柯到波特一直认为,除了西方思想史之外,疯狂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是启蒙运动对同质理性及其自然的标志和秩序权的信仰的副产品。缺乏理性构成了福柯在《疯狂与文明》中所谓的“意义过度”,而波特则接受并扩展了这一主张,声称“疯狂是千变万化的,因为思想本身不包含任何意义的终结。”斯科特(Scott)的疯子使读者陷入迷宫中,并揭示了一系列认知障碍,而这些障碍永远都不会与浪漫的想象力脱节。
首先,我想将斯科特对残疾人的同情追溯到两个初步的背景,即个人传记和社会历史背景,在返回韦弗利和《中洛特人的心脏》以寻求更持久的解释之前,我将首先谈到这些背景。首先,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的《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生平》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事实,这一事实经常被人们忽略:斯科特(Scott)在不列颠群岛写下了第一例有记录的脊髓灰质炎病例。他腿上的神经疾病不仅使他无法在爱丁堡高中进行早期运动,而且破灭了他后来成为一名士兵的希望。结果,它使斯科特开始撰写涉及他自己和他人的小说。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的前辈和安妮·卢瑟福(Anne Rutherford)分别是大律师父亲和圣公会母亲的第9个孩子和第7个儿子,在他出生时(1771年),他们已经埋葬了五个孩子。尽管律师占据了苏格兰社会的高层,斯科特家族也居住在爱丁堡大学附近的温德学院一所联排别墅的三楼,但距离欧洲一些最贫民窟仅几百码。从1750年到1780年,爱丁堡的人口呈指数级增长,而斯科特的头18个月是在最拥挤、最不卫生的地区度过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1773年初,斯科特遭受了三天的牙热病,并突然失去了右腿的所有感觉。 一位奶妈把这件事告诉了斯科特家人,孩子很快就被送到他祖父那里去了。他的祖父是一位医生,在桑迪·克诺威市30英里外的一个农场里工作。在那里他进行了各种治疗。在他自己写的“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早期回忆录”中,斯科特回忆起被困在绵羊尸体中的情景。 斯科特残疾最严重的方面,他称之为“我的跛足”,涉及一位有暴力倾向的女人,他的母亲将其与他一起送往了桑迪·诺恩(Rudyford)的卢瑟福医生的农场。以下轶事使用与女性精神错乱相关的暴力行为,不仅增强了斯科特希望传达的脆弱感,而且还通过一些苏格兰民俗来使自己的残疾历史更加黑暗:
履行这一重要使命的年轻女子已经把她的心抛在了身后,由一个野蛮的家伙抚养着,这很可能对她做了什么,对她说的比他想做的要多。 她变得非常渴望返回爱丁堡,而当我的母亲指出要留在爱丁堡的那一刻时,她对可怜的我怀有一种仇恨,原因是她被关押在桑迪-诺内。 我想,这让她有点发狂了,因为她向管家的老艾莉森·威尔逊(Alison Wilson)承认,她把我抬到了克雷格斯家族,这意味着在魔鬼的强烈诱惑下,她要用见到割断我的喉咙,把我埋在苔藓里hellip;hellip;当然,她被解雇了,后来我听说她成了一个疯子。
这则轶事充满了道听途说,同时也是对华兹华斯精神错乱的另一种暗示。到1826年,《抒情民谣》已经出版20多年了,斯科特的回忆录与华兹华斯的《荆棘》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这首民谣与斯科特笔下的人物马奇·野火(Madge Wildfire)有着相同的联系,而且还特写了一个埋在“美丽的苔藓山”下的“小宝贝”。但不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它只会加剧残疾造成危险和混乱的程度,而这种危险和混乱可能被认为是斯科特(个人)“自上而下的历史”,也就是说,从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记忆角度讲述的事件。
在这种回顾模式下,斯科特依靠自己作为讲故事者的优势战胜过去的逆境。他把少女的形象放在她的位置上,既提供了她的疯癫的原因(单恋),也提供了结果(监禁)。在斯科特(Scott)的一生中,似乎没有任何被认为“导致”精神错乱的因素的限制:菲利普·皮内尔(Phillipe Pinel)将体液过多作为原因,将“自发性腹泻”作为治疗方法,而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则将肉食性饮食视为点燃“脾气不合理”的导火索。长期以来,非理性一直被认为是恶魔附体、巫术,甚至在都铎王朝的英国精英教育圈子里,一个人的星相也会紊乱。在《魔鬼让我这么做》一书中,斯科特将这一观点应用到了威胁他生命的少女身上,我们看到了精神疾病,特别是精神错乱的许多表现中的第一个,这种精神错乱与恶魔主义交织在一起。
如果斯科特的人性化精神病患者动机并非完全具有说服力,那么在韦弗利的语境中,考虑斯科特所说的“那个时期的苏格兰思想”(W 47)。在19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发生了一些非凡而又全新的事:精神弱者开始为自己说话。大量研究证明了这一历史和法律事实。休斯敦依靠民事法庭的调查,或对那些被认为在精神上无能力的人进行“贿赂”,来展示白痴和疯子如何被聚在一起并发现精神错乱。这意味着精神上不健康的人被迫站出来在公开法庭上捍卫自己。“白痴”和“残暴”通常是由家庭成员发起的,尤其是在涉及财产的地方,并在诸如近亲会议和爱丁堡宪法法院等地方由法官聆听。在地方一级,这些案件不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手稿页,而且要求采用新的录取程序和制度化程序。休斯敦承认,苏格兰的人口在1819年仅占英格兰的五分之一,但在英格兰的90家私人持牌疯人院中,苏格兰的人口不到三分之一。 对于诸如错误的监禁以及谁应该为庇护的扩散支付确切费用之类的问题展开了辩论。
历史学家乔纳森·安德鲁斯(Jonathan Andrews)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观点,证明了对苏格兰庇护组织的日益加强的监督。他转向格拉斯哥皇家庇护所的案例记录,以分析对患者证词的日益重视。 直到1800年才需要这些笔记,只有根据1815年的《苏格兰疯人院法》才需要公共庇护来使记录正式化并接受国家监督。安德鲁斯(Andrews)声称,在苏格兰所有的精神病学机构中,格拉斯哥皇家(Glasgow Royal)是“保持记录的时代的领先者”。 患者记录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导致了过时的报告、第一人称的自白以及当患者死亡时的尸检报告的爆炸性增长。对于苏格兰精神病学和苏格兰文学而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第一人称推荐书出现之前,残疾人历史上就一直保持沉默,而斯科特可能希望填补这种沉默。
斯科特的小说结合了对精神病患者的这种新的理解;同时,他们极其依赖于18世纪末期已经流传的文本。斯科特(Scott)学者始终指出,个人和集体叙事的整合是《韦弗利》(Waverley)小说的某种标志,它取决于作者在文本之间的谨慎调解。尤其有两篇文章对司各特对白痴和疯子的同情表现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源于对感性的狂热崇拜。首先,亨利·麦肯齐(Henry Mackenzie)于1771年出版了《感觉的人》。斯科特(Scott)在1805年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的评论清楚地表明,麦肯齐的情感人物是“亲善美德”的典范:同情、耐心和内省。受霍格思1735年创作的《疯人院》的启发,哈雷,这个象征同情的人,看到疯人院的囚犯们感到震惊——“铁链的叮当声,他们的狂呼声”——强调了男性自我克制的极限。斯科特(Scott)同样将他对精神病患者的表述赋予野性的威胁,或者用麦肯齐(Mackenzie)的言语表达为“凶猛且难以控制”。 就像男性的柔弱一样,症状是感觉过剩。
塑造斯科特关于精神残疾的观点的第二篇文章是抒情歌谣,可以说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创刊物。其中虚构的精神病患者的肖像在这里尤为重要,因为斯科特的戴维和麦基都是基于华兹华斯时代的原型,例如“白痴男孩”中的约翰尼和“荆棘”中的玛莎·雷(均来自1798年)。当Madge哭泣地躺在稻草丛生的小屋里时,华兹华斯的话不仅巩固了她的躁狂症,而且阐明了玛莎·雷和她自己之间的相似之处。“她突然哭了起来,射精了,”斯科特写道,“是我!喂我!喂我!“直到最后,她呻吟着,抽泣着沉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37539],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